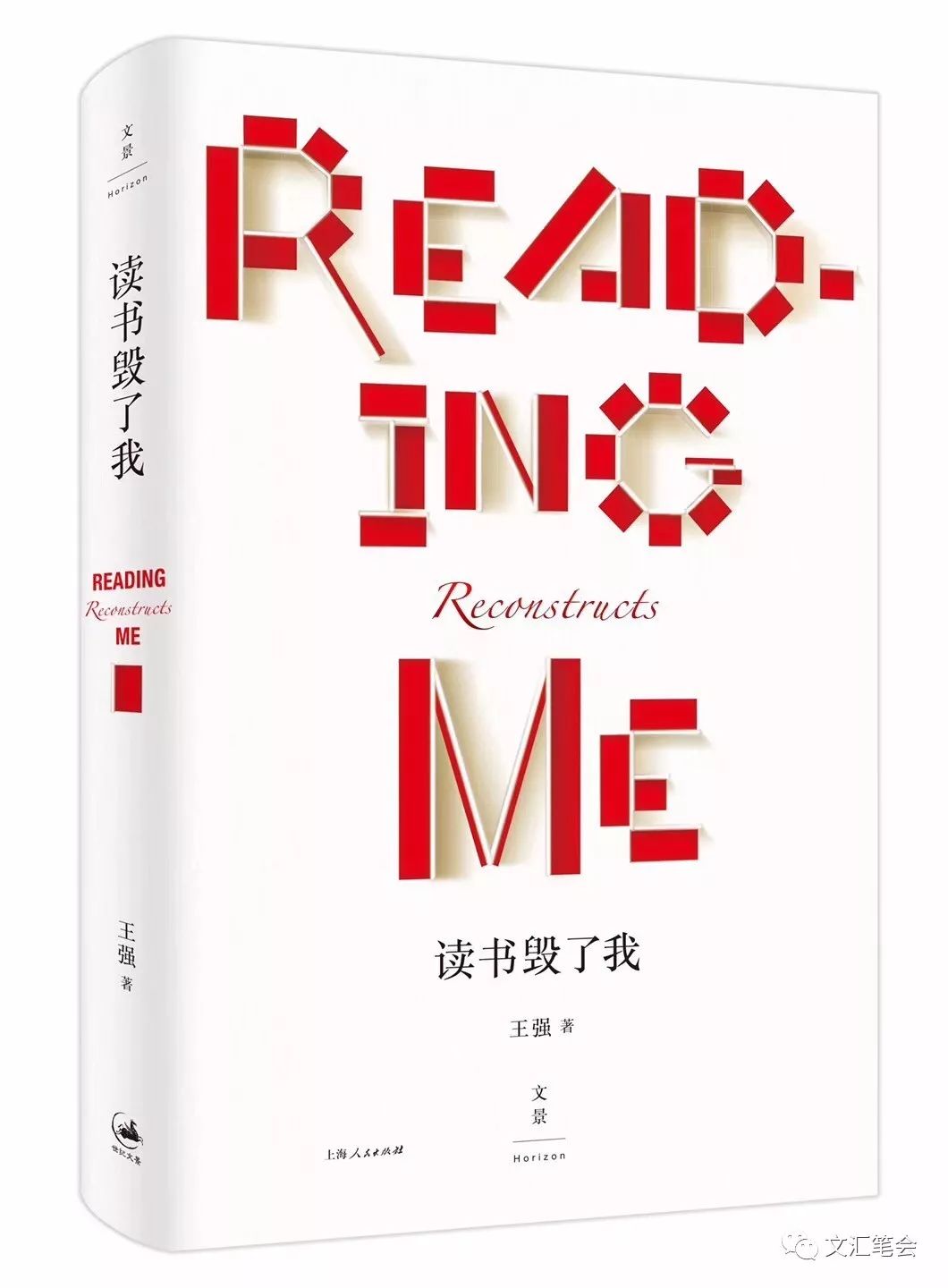
今年元旦,我从杂乱的书架上,取下王强《书之爱》,小三十二开本,二百余页,出版于千禧年一月。时隔十八年,我还能信手把它翻拣出来,捧在手中,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十八年间,它始终与一些书聚集在一起,供我日常工作和写作时翻读。它们都是“关于书的书”,其中包括书话、笔记、随笔,古今中外都有。在我的观念中,此为“知书”的一个重要门径,历来被爱书与藏书者看重。查尔斯·兰姆步入暮年时说:“现在我从书中得到的乐趣已经少了许多,但依然喜欢读谈书的书。”
王强是一位爱书成癖的人,他赞美兰姆的喜好,还推崇收藏家罗森巴赫的观点:“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游戏是爱的艺术,此后最令人愉悦的事情是书的收藏。”所以王强喜欢读“关于书的书”,乐于写“关于书的书”,他说:“那是爱书人关于书的情书,是阅读者关于爱书的告白。”
此时,我取下这本小书,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彼此在爱书观念上的相通。王强在《购书记》(1998年4月22日)文中称,时下书话流行,但缺少“书情、书魂,有知无识,有识无趣者居多”。在王强心目中,“入流之‘书话’需平心静气,细斟慢品而后可得。故虽落为文字,终当如饱学之士茶余饭后之闲聊,情动于中,发为声则如行云如流水”。文章及此,王强仅赞赏施康强的著作:《都市的茶客》和《第二壶茶》,前者正是“脉望”策划,即沈昌文、吴彬、赵丽雅和陆灏所编“书趣文丛”中著作。
对应过来,记得初见王强《书之爱》时,沈昌文赞不绝口,由此引发出许多创意。诸如读到《文学绞架下的雄鸡》,让我们知道扎米亚京《我们》,引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出版;读到《书之爱》,引出理查德·德·柏利《书之爱》的翻译出版;读到《厨烟里的大仲马》(2003年王强为《万象》写的文章,后来收入此书),勾起我们寻找大仲马《烹饪大辞典》版本的热情。还有2008年,我写文章《别吵了,索引时代已经降临》,落笔前我把王强《书之爱》找出来,认真阅读其中的文章《关于索引》。
有朋友说:将来,王强的这本小书一定会成为经典,经久流传。哪还用将来呢?在过去的十八年间,它一直为出版者和读者爱恋。不仅有繁体字版推出,还以《读书毁了我》为名增订出版,一版再版,在市场上始终保持着销售热度。
去年岁末,王强在微信上给我留言,谈到《读书毁了我》又要有新版推出,回忆小书初版故事,回忆书友交流的流年碎影,回忆积年藏书的乐趣与感慨,最终他说,晓群,为那一点念旧的情绪,你能否为新版写点什么?
就这样,我又取下它,再次翻读,见到阿尔伯特·哈伯德的金句:何谓经典?就是永远占据着书架却永远不被翻读的书。王强说,我们可以稍加改正:经典是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翻读不完的书。于是,我想到那些“关于书的书”,想到几十年来我从事出版工作,不断找寻那些经典旧著,把他们一本本整理出来,重新印刷、献给读者的故事。心中笃定:王强的这本小书,历经岁月,必然会再现那一幕“拿出来重印”的情景。
读下去,没想到十八年来的情绪,再一次笼罩我的身心:王强真是谜一样的人物!初读时我这样想,再读时我的感受依然如故。短短十几万字,到处都是关于书的伏笔与疑问。即使这些年当面交流,解开一些谜点,但还会有更多的问号涌现出来:
其一,读王强文字,时时给人激情四射的感觉,且与寻常阅读比较,似乎有些异样。比如他在《巴格达之行》中写道:“世界?一个没有目的地的目的地,一个巴格达中的巴格达,一种欲望中的欲望,一片梦境中渐渐清晰的梦境。这就是‘巴格达’所给予我们联想的全部魅力吗?”阅读这样的文字,你是否有一种跳跃的感觉?还有某种韵律在掌控着你的呼吸?最初我有些困惑,但最近有两件事情,让我有所感悟。一是王强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任北大学生艺术团第一任团长。后来的“新东方三驾马车”,最初正是在这里结交:徐小平是北大团委文化部部长,艺术团的组建者;俞敏洪是王强的同班同学、好朋友,艺术团的重要观众,王强调侃他为了看演出,时常来“帮艺术团拉大幕”。谈到艺术造诣,王强的声音和朗读最具天赋,后来他在新东方授课时,倾倒无数学子。再一是前些天,王强建议我编一本《伊索寓言》朗读版,中英文对照,分别由他来朗读。对于中文,他说要自己来重译,使之符合朗读的文字特点。哦,我明白了,上面那一段文字,你如果读出声音,就会感受到王强文字的风格所在。
其二,品王强文章,有说他西书读得太多,译著读得太多,思维与文风都受影响,时而文字有些“涩”,还有些“掉书袋”。于是问题来了,豆瓣网上竟然有数百条读者留言,网友们问题连连,其中不乏一些极好的追问和解读。我整理几段如下:
这是励志的书吗?不是,很少见到成功人士写这样的书。王强翻译过书吗?《购书记》(1997年4月14日):“今日始译惠京嘉之名著《中世纪的秋天》。用芝加哥新版。”能说王强“掉书袋”吗?一位书友写道:“王强在一篇文章里,掉书袋掉了那么多次,像钱锺书一样。虽然几乎要烦了,可是也不得不承认他读书多。”为什么许多书都没见过、没听说过?因为王强谈书多为外文原版书,多为藏家青睐的书,多为有趣且不落俗套的书,比如《穷理查的历书》《左撇子》《犹太书籍年鉴》《莎士比亚笔下的动物》和《误失类编》,让我们感到生疏。有书友写道:“这些书不被人提及,并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时代,不读书毁了太多人。”
其三,看王强选书,他把找书喻为“狩猎”。第一狩猎场是图书馆与学者文集,第二狩猎场是书店。漫步图书馆,他主张只记不借,记下书名、著者、出版商及时间。他称学者文集为“猎书地图”,他不喜欢有些学者“隐藏猎物的踪迹”,那是取巧和不自信的表现;他更喜欢像钱锺书、周作人那样坦诚的大学者,即使有人讥讽他们掉书袋、文抄公,但他们敢于把自己思想的轨迹昭示出来,他们的“引文”或“注脚”,正是猎书者的指南或向导。比如王强购买霭理士《性的心理学研究》七卷,还有理查德·伯顿英译《香园》和《天方夜谭》,都是读《周作人文集》记下的书目。
其四,听王强评书,评作者,评书店,评出版社,妙语极多,此处且择几例:陈原《书和人和我》三联版,外封雅,插图亦精;《生活与博物丛书》上古版,极厌恶此书题,不识货者只当是市面流行之常识一类;“柯灵散文四卷”远东版,柯文淡,余所素喜者;俞樾《茶香室丛抄》中华版,喜其名;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大版,其文简而内蕴丰富,谈英诗不可不读王佐良,谈英国文学史不可不读杨周翰;钟叔河《书前书后》海南版,文多短简,然具韵味,显然受知堂影响;梁实秋《槐园梦忆》,梁文简朴之至,悲情力透纸背;张谷若译《弃儿汤姆·琼斯史》译文版,张氏译文典雅,妙趣横生,译笔之传神胜于萧乾译本;赵萝蕤译《荒原》中国工人版,谓赵师每有名译脱手,时必神情恍惚;素喜黄裳之文,尤喜其书话;金岳霖文字大有英人宴谈(table-talk)之风格;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大手笔,笔淡而境出……
总之王强说书妙语不断,本想打住,然有数则关于董桥记载,煞是有趣:1999年2月,购得陈子善编《董桥文录》四川文艺版,他写道:“董桥正可佐酒。其文精、奇,虽略显脂粉,归之散文上品可也。”2001年12月去香港,他先在Page One书店买到陈子善编《董桥文集》三册,发现此编共十二卷十八册,又跑到天地图书购六册,到星光大厦购七册,最终在乐文书店全部购齐。一时累得双腿打颤,难以挪步,“然吾以为读香港董桥,港版才属正味”。
我知道王强与董桥相见很晚。2016年王强出版《书蠹牛津消夏记》;2017年7月香港书展,王强应邀赴港签售、演讲。其间林道群安排,王强与董桥首次见面。王强小董桥二十几岁,以晚辈相称。他们谈写作出书,只是相知的一个方面;在收藏西方典籍上,二位也有一比。董桥藏书积年,有见识,有财力,有华人收藏西书“第一人”之称号;王强藏书在美国,很少有人见过实物,因此成谜。席间王强拿起手机,请董桥看他藏书的数千张书影。董桥寻常为人彬彬有礼,很少开玩笑。那天他看着看着,突然抬起头来,笑着对王强说:“不看了。否则我会杀了你。”
作者:俞晓群
编辑:王秋童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