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993年3月,第一次见到李时人先生。
去参加研究生面试,有小小的紧张,还带点好奇。未来前行路途中,我们并不晓得会遇见谁,是谁,将引导并改变自己。春天的早上,我的授业恩师已然等待在文学所小楼,我正向他走去,却还不认识他。
房间烟味浓重。先生坐在一排书架前,一张油漆剥落的旧书桌,桌上一叠纸,一支笔,一截掐灭的纸烟逸着余气。低低木头窗户,紫玉兰枝叶遮掩了半扇窗。我孤零零坐在他对面椅子上,偷偷看他——一个敦实精壮汉子!!与我想象的瘦弱白皙书生不同:头发乌黑微卷,眉毛粗浓,单眼皮,皮肤粗糙略黑,像是个劳动者,身上混合着粗朴而文雅的气质。他嘴唇紧抿,嘴角有一道疤痕(至今不知他何时因何留下),这让他显得严毅。奇怪的是,我并不怕他。因为他的眼神柔和而宽容,含着隐隐的笑意。他甚至有点害羞局促,倒好像不是我来面试,而是他自己进入考场。
提问与回答过程,大多忘记了。只记得先生问我,在复旦本科读的是政治学,为何要报考古代文学专业呀?我答曰喜欢,自己胡乱旁听些中文系课程,又胡乱读书,逮什么读什么。先生就笑起来,朗声说,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思维开阔,能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新鲜血液;又说,喜欢读书最要紧,乱读书更好。那一瞬间,春天的年轻的光亮斜斜入窗,静谧空间,流动着香氛,我能感觉,与先生心意相通。假如先生取中我,或许就是冲着我身上有那么一点点对读书的热诚与单纯吧?后来知道,先生自己就是旁听杂收、乱读书出来的,一个人搞研究,热爱第一要紧。
先生前半生,具传奇色彩。他上世纪60年代进高中,后学业中断,辗转在运输队、工程队、玻璃厂当工人。干粗活之余,先生不辍读书,但得书籍,便偷偷阅读。到1980年,先生前去报考研究生,却因其才华学识,被徐州师范学院直接聘为教师;1986年,又被破格聘为副教授;1989年,他调到上海师范大学,于1992年再次破格晋升为教授,1993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我参加面试,正是1993年,我与师兄,成为先生的开门弟子。在我惴惴不安前去面试时,先生也正好奇于他的第一批弟子会是怎样的吧?这是他害羞局促的缘由?先生后来招收了百来个硕士博士生,他们,对先生的记忆,一定与我的不同。
时隔二十五年,我很想问先生当时的想法,告诉他春天那场面试我的感觉,却再也没有机会了。先生病重,握着我的手,失声哭泣。在我眼中心里,刚强、严毅、端谨、矜持的先生,一个巍然不为各种所动的男子汉,竟在我面前,弱小如婴孩。我无法知道先生此时想到些什么,或许,看见我,先生想起了他青壮年的种种抱负?是念及他开门收弟子的第一个春天?还有对他未完成的学术研究计划的心有不甘?
2
1993年到1996年,三年间,每周有一二天午后,师兄朱振武都会用自行车载我,前往先生位于钦州南路的家里上课。自行车滑行校园,闪过一座座楼房,花树的婆娑开落、道路的弯曲平直,一个个瞬间,串成我的青葱岁月。
上课时,一般是就老师开列的书籍,我和师兄先分别讲谈阅读体会,先生最后点拨、提升。先生主张因材施教。比如,比起本科古代文学出身的,我的阅读面较为广杂,长于理论思辨,先生鼓励我发散思维,畅所欲言,但有片言只语出新跳脱,先生就很高兴。但他又强调立足文学、贴近文本,否则研究就好似建立在沙盘上,基础不牢。就我所长,先生鼓励我论文做《冯梦龙与晚明思想》。又具体指导:读“三言”时,强调关注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研究冯梦龙经史思想,强调关注当时思潮。论述思辨之外,先生又要求我立足文本,做好考据功夫,诸如比对“三言”与宋元话本的关联,考察文言与白话的互为演变;考据冯梦龙交游,寻找其与晚明思潮之关联。先生主张,研究与创作,都要立意高远、下笔有据、思辨严密、博通精微。
与教学一样,先生自己做研究也主张:考论兼得,博通精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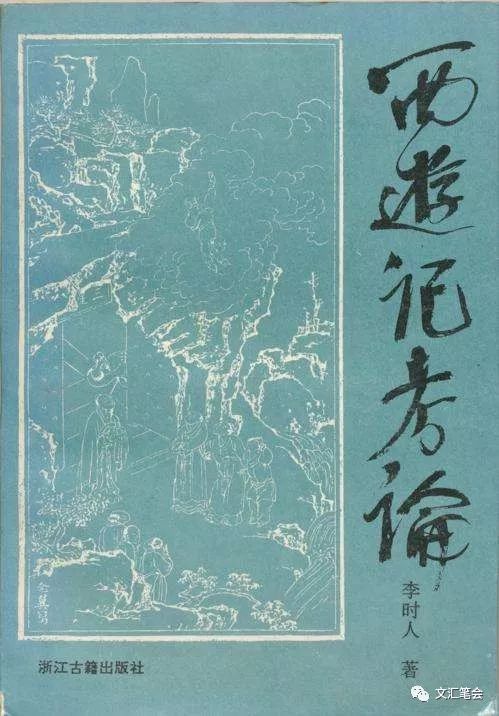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初,先生偏重撰文论说,《西游记考论》《金瓶梅新论》等,在业内广有影响。近二十年,他几乎将所有心血扑在两套大书的整理编撰校订上。《全唐五代小说》,再版为八卷本,是一部可与《全唐诗》《全唐文》鼎足而立的唐代文学三大总集,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做了重要的整理、积累、铺垫。先生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搜罗出明代文学家二万余人,编著《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160万字,为明代文学家三千多人撰写词条,大大推进了明代文学研究。
3
恩师生于春天,逝于春天。
先生没料到,再次进医院一呆九个多月,竟至一病不起。他在病床上,完成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校样审读,得见这部耗费十几年心血的大书出版。他虚弱地向我伸出四根枯瘦手指,那是指业已交稿、年内即将出版的四部书:《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的传播与影响》《唐人小说选》《崔致远全集》《点石集》。但还有许多计划未竟:“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即将结项;“宋元小说全编”“明人序跋集”等中期目标、“中国小说史”等学术远景均在筹划中……先生躺在病床上,心急如焚,他多想根除病源,回到书房工作。
“如何走出医院?”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2018年3月28日上午,先生溘然长逝。望着面容平静,仰卧在病榻上一动不动的先生,我无端想起苏东坡的故事。苏东坡弥留之际,方丈要他想想来生,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来生,有什么用?”方丈还是要他想,他只说:“勉强想就错了。”在东坡看来,是否有来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今生,生死之事,顺乎自然。
四十多年来,先生品三国,论水浒,考西游记,证金瓶梅,校注游仙窟、崔致远全集,撰集全唐五代小说,考订撰写明代文学家,又关注唐诗话、变文、讲经文、佛典,著述达二十多部。先生的今生,足够努力,足够圆满。

4
先生喜欢在家里而非办公室给我们上课。有时讲得兴起,眼睛会闪闪发亮,还会撸起袖子,手臂乱舞,边抽烟边讲,嗓门越来越响……在别处做事的师母听到了,便会叫起来:轻点哇,烟灰不要乱弹哇……一下午转眼过去,有时拖到晚饭时间还没下课,师母就会留我们一道吃饭。
师母烧一手好菜,性子活泼,老师很是宠她;她说话清脆如珠玉落地,先生此时只是唯唯不语,微笑静听。先生好抽烟,也喜饮酒,我们会陪着喝一点。好几次,遇见何满子先生来,留晚饭,我与师兄叨陪,炒菜落锅声响,葱姜爆炒香气,师母笑盈盈上菜,有老师必不可少的鱼,有他爱喝的洋河。何先生多喝了几盅,乐得像个孩子,兴之所至,谈古论今;先生此时,也不若常时那般端谨,一手执烟,一边饮酒,谈笑晏晏,不时豪放大笑,黑宽面庞微微泛红,眉毛更为粗浓,很有点《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风神。
我猜想,我们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遵循的是传统师门传承。孔子与弟子,起坐饮食一处,歌唱奔走相随。我们与恩师,虽无法时时起坐相随,但先生秉承传统教育,以为师长不仅要在知识层面传道受业解惑,更要在日用生活中言传身教;弟子的学习,也不仅在文字知识上,更在于实践中、在日用生活中受先生潜移默化。在传统师门关系中,师父如父,师母如母,李根当时年仅10岁,即是我们的幼弟。若如现代教育,老师与弟子的关系,仅在课堂上,离开课堂,即是独立自我。近年更有因师长叫弟子做点杂事,即被媒体诟病为“奴役学生”,大加鞭笞。导师固然不应过分使唤弟子,但在传统师门关系中,师生之间的生活是相当亲密的,这种亲密,如今想来,是多么难得的温暖。
2018年4月1日初稿完成于先生书房,
定稿于4月3日恩师生日
作者:赵荔红
编辑:王秋童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