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书作者在1938年被选为诺尔曼·白求恩的助手,来到中国工作,无意中见证了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作者略述了她在加拿大的成长经历以及早期在旧中国教会医院的工作经历,并着重记录了1938和1939这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代中中国发生的各种冒险和政治阴谋。书中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根据地的生存实况,战争年代的毛泽东,八路军的近景特写,以及被红色中国誉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白求恩的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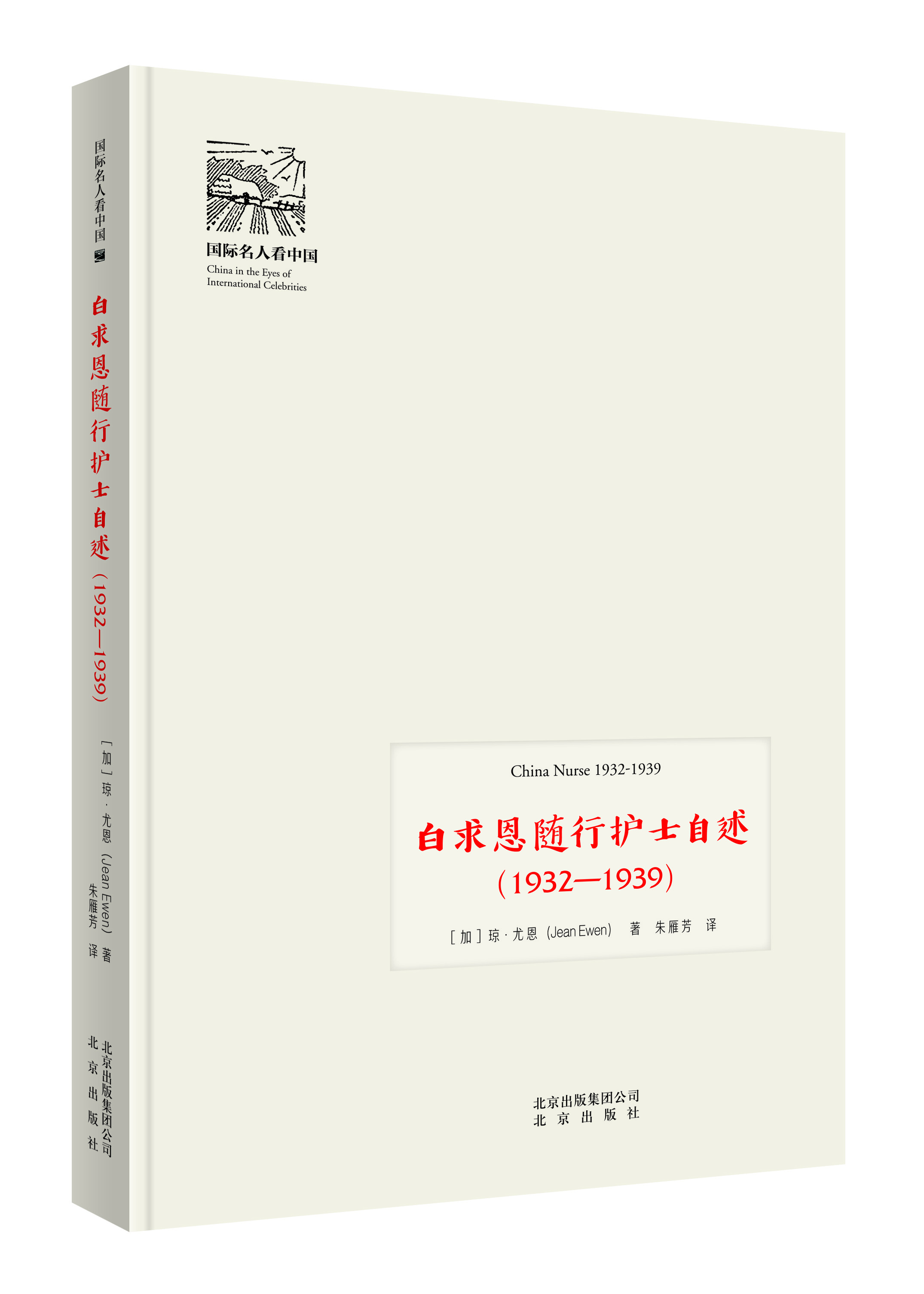
《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 1932—1939》
[加] 琼·尤恩著
朱雁芳译
北京出版社出版
与朱德和林伯渠畅谈
坐在卡车里,奔驰在陕西的公路上的时候,根本就无法欣赏乡村的景色,因为地上的融雪被碾压成了一道道深深的车辙。八路军的司机对路上的坑坑洼洼却一点儿也不在乎。
天黑的时候,我们经过西安城郊壮观的汉陵和周陵。不久,面前就出现了坚固而高大的石砌城墙。守在西安城门口的气势汹汹的卫兵检查了我们的通行证和护照。
一进城门,我们就看见大街上的铺子灯火通明,饭馆的大门敞开,飘出诱人的香味,一派极具中国特色的景象。卡车继续向前冲,完全不顾街上的鸡犬和孩子,直到走到一家高级浴池门前才停下来。
白求恩大夫和军需官走进一间蒸汽室,我则进了“女部”的门。一位顾客一间小浴室,里面有一只特大浴缸,盛着清澈的热水,还有浴巾和香皂。洗完澡后,我们在前厅碰头。
“哟,”白求恩大夫说,“你已经不像刚从汉口出发‘旅游’时的那个人了。”
我回敬他说:“你也一点儿不像在香港走下‘日本皇后’号轮船的那个衣冠楚楚的家伙了。”
“太不可思议了!”他说,“就像过了100年!”
军需官带我们乘人力车来到八路军办事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林伯渠在那里给我们接风。林伯渠和他的工作人员正在吃晚饭。他邀请我们一起吃,但又说他已经接到通知,在西安宾馆已经为我们预订了一桌丰盛的美国大餐。
到了西安宾馆——当地第一流的饭店,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才适应了那些崭新的桌布、刀叉、玻璃杯以及真正的面包、奶油和冰激凌!
餐厅里的其他几位外国客人走过来向我们做自我介绍:一位是国际联盟流行病防治小组的组长穆瑟大夫,一位是小组里的内科医生埃里克·兰多厄,还有一位年轻的工程师。他们问了许多关于生活条件方面的问题。大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喝着咖啡,吃着甜点。后来,饭店经理走过来请我们退席,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几乎快半夜了。
但对于我们来说,夜晚才刚刚开始呢!我们回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正等着我们继续谈话。他曾坐牢多年。他说他那口流利的英语是坐牢时学的,是一位每周去监狱一两次的教士教他的。虽然已经上了年纪,头发也白了,但是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神采奕奕,像年轻人一样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会找到许多话题和笑料,包括他自己的。
林伯渠问白求恩大夫:“你们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路上走了多少天?我们还以为你们已经死了,都通知你们那边了。”他继续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美国报纸上说一个月以前你们就失踪了,估计已经死亡。”他递给我们一份1938年3月12日的《芝加哥论坛报》。的确,上面的一篇文章说我们都已死亡,并且还刊登了白求恩大夫的照片。
那天,朱德刚从延安过来,参加西安的一个会议。趁他还没有被战士们围住不放,林伯渠提议我们先见见他。朱德就像战士们的长辈,八路军战士,特别是红军老战士都很崇敬他。他不佩戴军阶徽章,任何一个“小鬼”都可以随便跟他打招呼而不会受到申斥。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个子不高,身材粗壮。他的名字都足以让日本人和国民党政府的那些奴才们吓得心惊胆战。
朱德大概50岁出头的年纪,却已满脸风霜。他咧开大嘴,笑着迎接白求恩大夫。他们拥抱了一下,并各自用自己的语言说:“让我好好看看你!”说着两人都开怀大笑,互表钦佩之情。只有男人互相认可对方时才会这样做。朱德、林伯渠和白求恩大夫一直畅谈到第二天清晨。因为林伯渠的英语说得很好,不用我翻译,因此我就离开了。他们讨论在五台山开办医院的事。
奔赴延安
除了剩下需要打包的铺盖卷和个人用品,所有运往延安的东西都已经在头一天夜里装车了。天还没亮,卡车就轰隆隆地开出了西安东门。按照传统风俗,西安没有北门,因为古人认为不干净的东西都是从北面来的。一旦出了城门,要想找到路就只能沿着城墙走了。
出城后,我们让司机在景教大寺院暂停一会儿,进去参观那里的梵文石碑。这些石碑记载了早期基督教徒穿越欧亚大陆,逃避古罗马皇帝迫害的史实。碑文已经磨损不堪,但上面依稀可辨的字迹仍能证明景教徒何时何地迁来这里的悲惨历史。如同现在开封有犹太人一样,这些石碑是西方与中国早期接触的证据。
卡车驶过一些金字塔形的巨大陵墓。我们意识到,在西安的暂歇结束了,新的生活即将开始。这一带的乡村看起来既宁静又繁荣。很难想象就在东边几千米的黄河对岸,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同受太阳照耀,那边却只有死亡和荒凉。
卡车之行对白求恩大夫似乎没什么影响,一连3天纵贯陕西的长途跋涉在他身上看不出任何疲劳的痕迹,也许是他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邂逅给了他鼓舞和力量。他似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思想总是跑得很远很远。旅途中,他写下了一些文字,说是日后修改好要发表在加拿大的报刊上。他的文字能很好地表达他的思想,文体十分优美。
第三天早晨,卡车很早就上了路。司机们想在天黑以前赶到延安,一路飞奔,没一会儿我们身上就蒙上了一层尘土。之后到了富平,这里属于边界地带,是所谓通往红色革命区的大门,距离延安约16千米。
在这里,所有过往人员都要接受彻底检查,比通过国境线还要麻烦。但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时有可疑分子混进来,其中不但有日本特务,还有国民党的破坏分子。
负责检查的军官非常仔细地检查了我们的行李,但一点儿也不粗暴无礼。两辆卡车一共花了一个半小时。最后他向我们敬礼,挥手放行。
公路沿着植被茂密的延河河谷通往延安。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农民们正忙着犁田,一些孩子在放羊赶鹅。当我们快要进入富有传奇色彩的城市、中国革命的摇篮之时,我必须承认,我心里有点儿激动,同时也夹杂着一点儿恐惧。
古代中国建造长城的时候,延安是监工和他们的亲信奴仆居住的地方。进城的道路和四周的城墙,都是用从远处运来的巨大石板筑成的。出富平城不远就能看见南城门的塔楼。
突然,卡车又停下了。一个武装战士检查了我们的通行证。然后,他转向白求恩大夫说:“请允许我好好看看您,因为我怕不能再亲眼看见像您这样的传奇人物了。您是来帮助我们的。”我请白求恩大夫下车,跟那个小伙子说几句话。这个小小的仪式结束后,那战士便挥手让我们继续前进。
遇见马海德和李德
驶入延安的城门,我们不禁有点儿吃惊,原来延安这么小啊!灰暗的街道上排列着更加灰暗的店铺和饭馆。一大清早,全城的人就举着旗、架好鼓,等候白求恩大夫的到来。一位面容和善、举止文雅的人前来迎接我们,他是马海德医生,黎巴嫩出生的美国人,早在中国内战时期就加入红军了,还在甘肃省参加了长征。
马同志带我们到一家最新的合作饭馆吃晚饭,这家饭馆最拿手的是又宽又厚的粗面条。我这样说绝无贬低之意,倒是赞赏有加,因为中国的厨师是世界上最巧妙的手艺人,他们能把面条做得看起来,甚至吃起来,不像面条而是别的什么珍馐美味一样。吃饱了之后,我们应马海德的邀请到他的窑洞里喝咖啡。他很肯定地对我们说,这是美国咖啡,日本天皇的礼物,但运来中国后落到游击队手里,偏偏游击队是不喜欢喝咖啡的。这是我们离开西安后第一次喝咖啡,说真的,刚喝到嘴里的时候还有点儿晕乎乎的呢!
我们坐着闲聊的时候,李德大步走了进来。他是一个高个子、白肤金发的德国人,头发稀疏,浅蓝色的眼睛上戴着一副很厚的眼镜,一副哥萨克人似的扬扬自得的神气。
我们同李德和马海德大夫一直谈到11点多。这时,“小龅牙”进来说,我们要住在招待所,一切都安排好了。招待所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一个高级的住所,因此,当我发现我的卧室竟然没有门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吃惊。屋里有两盏豆油灯,糊纸的窗户,夯实的泥地。墙壁刚粉刷过,挂着蒋介石夫妇的画像和国民党的小旗,对面的墙上挂着一面大红旗。在这里,人们很重视统一战线——甚至还歌颂呢。我更加确定已经到了延安,到了新的中国。
见毛主席
我正盘算第二天到城里走一走、看一看,一个年轻人出现在门口,向我敬礼,说:“同志,很抱歉,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可是毛主席想尽快见到白求恩大夫。”我赶紧跑去通知白求恩大夫,说毛泽东派人来找他了。这时,他本来已经上床了,但不到一分钟,就重新穿好了衣服。
他走过我的房门,对我说,“哦,你就不必去了。”但我马上坚决而且语带讥讽地回答他:“既然我没有被正式开除出这个所谓的医疗组,我认为我就有资格去,有资格被接见。”
这位好大夫向我极力解释,说他所说的“不必去”并不是我所理解的意思。
于是,我也去见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了,尽管我没有任何证书要呈递。陪我们去毛主席住处的人向我们解释说,主席习惯夜间工作,从半夜开始,有时直到第二天早晨八九点钟,因为这段时间最安静。他还说,主席除了接见重要人物,通常不会客。
穿行在寂静漆黑的小巷,哨兵们时不时突然的一声“谁呀”把我吓一跳。毛主席窑洞外的警卫战士撩起一块厚厚的棉帘子(那里没有门),我们就向黑乎乎的窑洞里走去。
漆黑的窑洞里边,有一张制作粗糙的桌子,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昏黄摇曳的烛光辉映着堆积在桌上的一大摞书籍、文件,低矮的窑顶和经过砸实的地面。桌边站着一个人,他的手放在一本书的边缘上,脸对着窑洞口。同延安所有战士的穿着一样,一套蓝布制服,只是头上戴了一顶带红色五角星的帽子。他的身影映在墙上,似乎更加突显了他身材的高大。晃动的烛光把一切都照得若隐若现,为我们的会面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毛主席一面微笑着向我们走来,一面说:“欢迎,欢迎!”他向白求恩大夫伸出手来,白求恩大夫也伸出手去,接受他的欢迎。主席的双手修长细腻,像女性的手一样柔软。他们无言地互相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像兄弟似的拥抱。主席的额头很宽,黑发浓密。当我们在桌子边——他和秘书刚才工作过的地方——坐下时,他那感情丰富的嘴角洋溢着微笑。那位秘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就不用我担任翻译了。毛主席只说中国话,而且似乎也没有兴趣学习外语。说过了几句关于天气的话以及我们在陕西的艰苦日子后,白求恩大夫便把加拿大共产党的证书交给毛主席。他的证书印在一方白绸上,上面有党书记蒂姆·巴克的签字,还盖有章。毛主席以一种近乎崇敬的态度郑重其事地接过去,说:“我们将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了!”直到这时,毛主席才问了我一句,我的中国话说得这么好,是从哪儿学的。
话题照例转到了五台山,那里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十分需要医疗援助。白求恩大夫将成为那里的福音,但他不敢肯定我能否应付得来,因为那里的生活很艰苦。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们一杯接一杯喝茶,一把又一把吃花生和葵花子。这些都是这个贫瘠的地方通常招待客人吃的东西,花生既有营养又很便宜。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问我:“你看白求恩大夫长得像不像列宁?”这时,他站起身来走到可以看到大夫侧影的地方。
“像呀,只不过白求恩大夫的后脑勺比列宁的好看。”我说。
秘书把我和主席的话翻译给白求恩大夫听,用“高兴”这样的字眼都不够形容他的感受。他荣幸而得意,即便有时他的确很像列宁。后来,我们4个人讨论起秃顶的问题来,但谈了很久也得不出一个合理的结论。不知不觉间,黑夜过去,已经到了4月2日。东方的山峦之巅,曙光泛起,挤走了黑暗。远处,公鸡打鸣报晓。
回到招待所时,我满肚子都是茶水和花生,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一直睡到中午。我醒来时,白求恩大夫已经被延安的乡亲们请去参加专门为他举办的接风宴会了。据“小鬼”说,白求恩大夫10点以前就走了。
此后几天,白求恩大夫的日程一直排得满满的:发表演说,参加宴会,接见杂志、报纸和墙报的记者。此外,他还同塔斯社的一位独臂记者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这位记者是我在延安见到的唯一的苏联人,而国民党却说苏联人在延安到处都是。
一天下午,白求恩大夫去了抗大,给学生做了长时间的演讲,又花了更多的时间解答问题。我没有跟他去,因为我感觉他并不喜欢我像影子一样总跟着他。
我不知道白求恩大夫是怎样保持他给自己规定的生活作息的,他似乎从来不曾懈怠过一下。加拿大共产党的证书为他打开了这个国度中所有的大门。人们到处找他,称他为敬爱的老师,而他自认为和抗大其他学员一样,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摘自《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 1932—1939》,北京出版社出版
作者:[加] 琼·尤恩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徐坚忠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