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求恩大夫
该书作者在1938年被选为诺尔曼•白求恩的助手,来到中国工作,无意中见证了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作者略述了她在加拿大的成长经历以及早期在旧中国教会医院的工作经历,并着重记录了1938和1939这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代中中国发生的各种冒险和政治阴谋。书中记载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根据地的生存实况,战争年代的毛泽东,八路军的近景特写,以及被红色中国誉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白求恩的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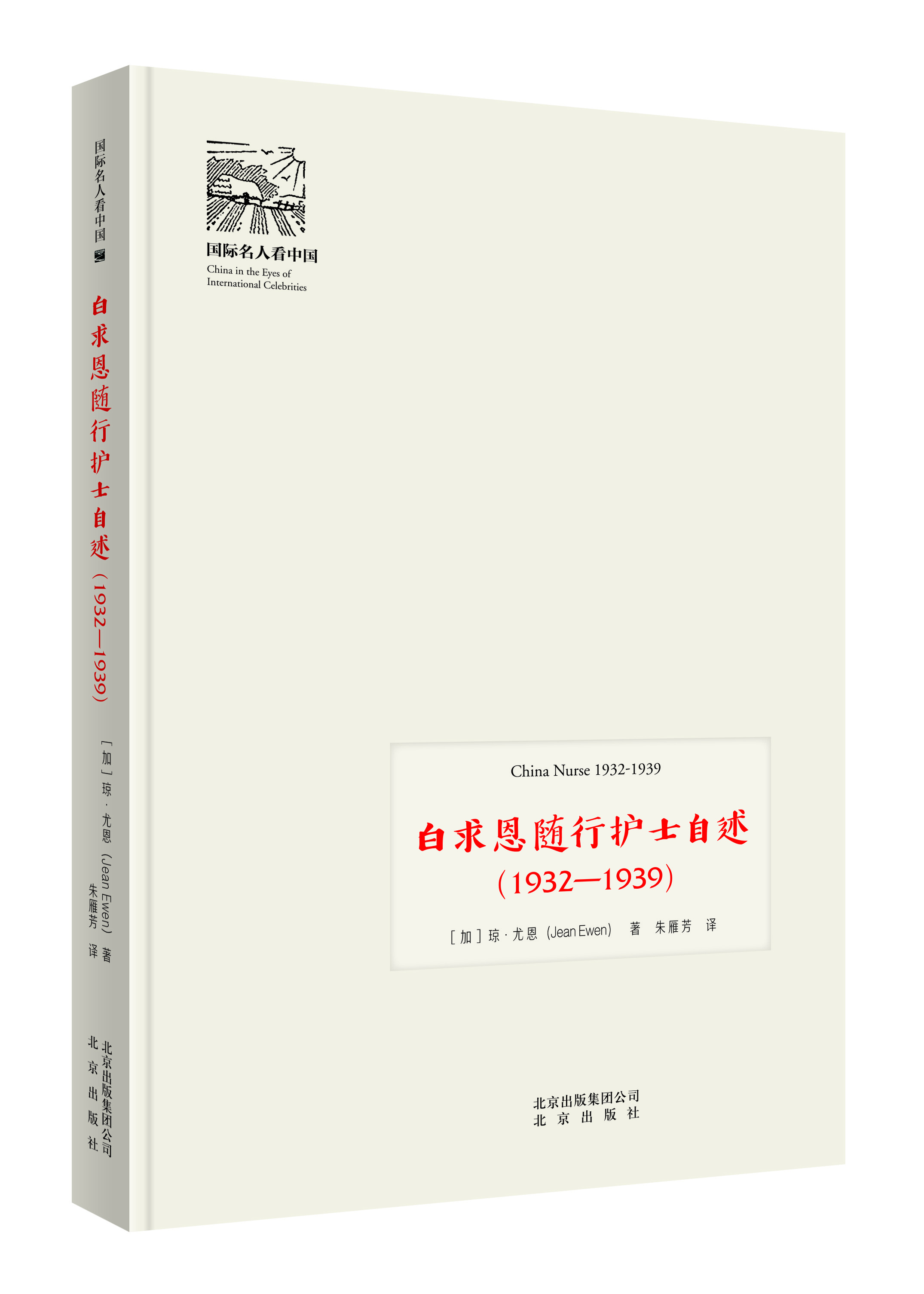
《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 : 1932—1939》
[加] 琼·尤恩著
朱雁芳译
北京出版社出版
贺龙叫我“洋鬼子”
我们转移到岚县——贺龙的司令部所在地时,6月差不多要过去了。很快副官让我们在司令员的房门口等候接见。我们清楚地听到副官喊报告,然后说,他带来了弹药、牛肉罐头、药品、战士、夏季服装、5个卫生员以及1个外国女人。
“什么?”一个深沉的男声问道。
“一个外国女人。”副官不慌不忙地回答。
然后,一个“小鬼”把我们领进贺龙的私人房间,他是八路军一二〇师的司令员。
他打量了我一下问道:“嗯,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在湖北抓了两个教士并给他们洗脑的那个人。”我回答道。我听说同贺龙谈这个话题总能使气氛活跃起来。我还问他,据说他曾让教士向八路军战士布道是不是真的。
“不错,”他答道,“他们都是好人呀。”
贺龙,现在正庄严地站在我面前,个子不很高,宽肩膀,一副桀骜不驯的神气。他方脸庞,浓眉毛,眼睛明亮,嘴巴大而富有表情,嘴唇上还有两撇引以为豪的胡子。他常含着一只黑烟斗。这烟斗很少点着,待谈得投机之时,便在嘴角挪来挪去。他年已50岁,但长得很年轻,行动从容潇洒,举止轻松灵活。在国民革命时期,他率领的部队曾并入国民革命军之中。
我问他是不是曾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过一艘摩托登陆艇,现在被称为“贺龙的海军”。那艘登陆艇被用来在湖泊中指挥游击队打国民党。
有好多年,贺龙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10次努力,终于被接受了。他能阅读书报,而且还自修古文。外表上,他是一个像岩石一样坚硬的汉子,但只要打破这层硬壳,据说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温情的男儿。
萧克——副司令兼政委走了进来,说他刚刚听到有个外国女人跟贺龙在一起,竟有这种事!萧克是一个身形瘦长、活泼好动的人。他说话很快而且说话时常常走来走去,老是用手比画着。我相信要是他的手没有了,他就说不出话了。他比贺龙年轻,大概30多岁或40岁出头,要不是脸上有粉刺,还是很英俊的。他很想在下巴留些胡子,可惜不能如愿。
两位首长对我住在哪儿合适议论了一通,因为他们不愿意我待在军营里。贺司令把陶东叫了来。陶东是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女教师,业余当戏剧导演。她走进房间看见我,眼神里充满惊讶。贺龙把情况给她交代清楚后,说道:“这个洋鬼子是来看护咱们的伤员的。你把她带走,需要什么就给她什么。”从此以后,我这个“洋鬼子”的名字就被叫开了,老乡们和战士们都这样叫我,但并无恶意。
住在岚县的第一晚,我刚躺下就响起了讨厌的没完没了的敲门声,大家都被吵醒了。面前出现了令我惊异的一幕:一个农民装束的人,披着一件日本军大衣,仲夏里竟是冬天的装扮。他的双手抱着一大堆东西:美国咖啡、香烟、饼干和巧克力酱。他说他的游击队拦截了一支日本运输队,大约有20辆卡车,上面载满了给养品和好吃的东西。他行个礼便转身走了。第二天,我在司令部的院子里看到汽车轮胎、车轮、电池以及各种汽车零件堆满了一地。能用的就留下,不能用的诸如马蹄钉、挡泥板等就砸碎用来制造炮弹,然后“物归原主”。
贺龙的马
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司令部的两张长桌子上吃饭。饭后,大家都到运动场去打网球或排球,这是人们,特别是姑娘们,最喜爱的运动。球场管理得很不错。赛马也很受欢迎。马儿都是被牵到运动场并且上好了马鞍的。
有一次,贺龙让我骑他的马。我想,他大概想看我掉下马背出丑吧。但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我稳稳当当地坐在马鞍上。马儿在空地上兜圈子,打响鼻儿,搔地,尥蹶子。后来,它大概看出来我并不想下去,就轻快地奔跑了一段。但只跑了一会儿便站住不动了。贺龙说我是第一个骑这匹马的女人。我知道,这匹马并不喜欢让女人骑。
运动场上,有两匹经历过长征的牲口:一匹老马和一头骡子。
“有两件东西,红军在长征时没有损失,那就是骡子和女人。”贺龙开玩笑说,“在伤亡名单上,没有女人,也没有骡子。”
然后,贺司令说他要为我表演他的绝招——这样的表演也许我今后再也看不到了。一个“小鬼”吹响了空袭警报,马群便腾空跃起,骑士们下了马,把缰绳越过马头稳稳地拽紧。这时,所有的马都屈下一条腿,接着又屈下另一条腿,然后,每匹马都臀部着地,侧身躺在地上。没有发出解除警报以前,它们就这样躺着不动。但一听到军号吹出长音,它们就立刻站起来了。
到息马坡执行任务
8月的一个下午,贺龙司令来到医疗站,还真是稀罕。他说东北方向战斗频繁,有不少游击队员负了伤,希望我们派些人到那儿去。我们大家都为有此机会而高兴得跳起来。
交代好谁也不准擅离指定的地区后,白天的炎热一过去,我们就出发了。下午5点左右,收拾好急救包,钟大夫、李大夫、一个卫生员和我便骑马出发了。一切都按命令执行。我们和走在前头的尖兵保持一大段距离。沿途的农民向我们要治疥癣和沙眼的药,我们还给受伤的人治伤。麻疹正在儿童中大暴发。实际上,每家都有得病的,还有不少有并发症。有些年轻人成了盲人或半盲,有的腿脚水肿,有的得了心脏病并发症。营养不良是各个地区最大的问题。人们吃不饱、没有钱买粮食,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有些地方本来就多灾多难,这场血腥战争更是给老百姓的苦难雪上加霜。我们试图向妇女们讲解用“隔离”的办法来解决流行病的问题,但她们理解不了。
受伤的老百姓见到我们很高兴。从来没有任何医生或者教会的人给他们看病。很难想象这片肥沃富饶的土地,竟然贫瘠得无法用文字形容。我不知道50年之后,这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情况应该不会更糟了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出发到一个叫息马坡的镇上去。这里的乡村景色同南边的临汾不无相似之处。忽然,我们闻到一股恶臭,而且每前进一步,臭味就越重。4个战士骑马奔向我们,一定要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还说附近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李大夫、钟大夫打算返回,但我想再往前走走,看看日军留下的“礼物”。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息马坡。空荡荡的教堂窗户就像骷髅上的窟窿。我们决定还是先看看教堂的院子。走进大门,只见守门人的尸体斜靠着墙壁还立在那儿守着入口,在他的旁边,有一个姑娘,也许是个教义问答员,头被子弹打穿了。他们的衣服渗满了血,脸和手已经变黑了,臭味刺鼻。在教堂后边的院子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老人的尸体,不远处还有两具童尸被扔进一个猪槽里。小教堂里所有的东西——窗户、椅子、书籍、碟子和祭服,全都被打碎、撕破了。那盏长明灯盛满了人的粪便被挂在圣特里萨神像的脖子上。整个教堂满目疮痍,地板上全是马粪。本堂教士不见了踪影。
两位大夫让战士们出去。因为新负伤的伤员现在已经往这边赶来,我们决定不再往前走了。谁也没有胃口吃饭,但村外的老百姓给我们送来了酒和烧饼,说吃点儿东西对身体有好处。他们觉得本堂教士可能被抓去了,教士是荷兰人,老乡们原以为他是不会出事的,因为日本兵不会伤害洋人。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经常碰到类似的错误看法。
我们3个人一面安排伤员们赶快休息,一面着手去除盖在他们伤口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些伤员的伤口是用白纸当纱布包着的;有的曾用牙粉来止血,效果很好,但问题是现在如何把那些硬痂揭掉而又不会重新引起出血。
我们返回岚县时,速度很快。我们始终走在担架队前头。钟大夫和李大夫不时走到担架队伍中,给伤员发止痛药,或者给他们送茶。
包括贺龙司令在内,司令部的人为我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贺龙还请我们吃晚饭。席间,我们向他讲述了我们的经历。后来,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拍了拍我的头,说:“我说,‘洋鬼子’,当日本军队侵略你们国家时,你们的人民会怎么想呢?”这个问题确实该好好想想,尤其是那些住在中国大城市租界里的白人该想一想,难道他们还认为由于自己的肤色是白的,日本兵就会对他们发善心吗?
——摘编自《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 : 1932—1939》,北京出版社出版
作者:[加] 琼·尤恩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徐坚忠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