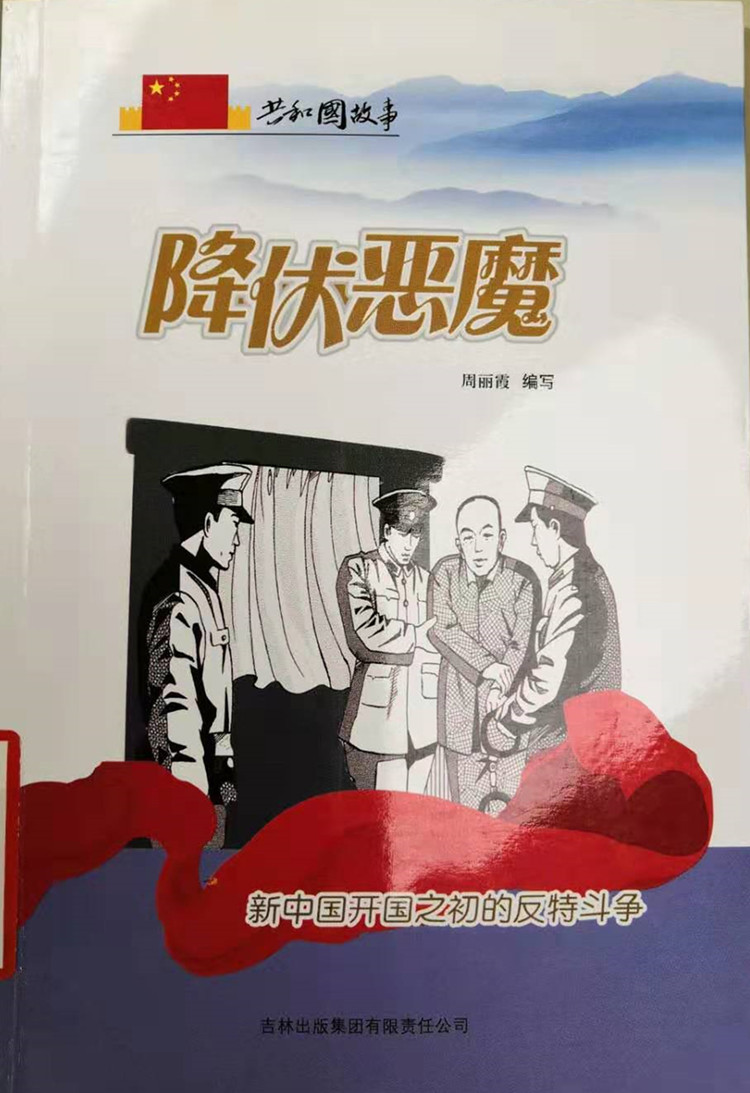
1950年春末的一天深夜,就在北京市计兆祥家的“北平潜伏台”被市公安局缴获的几个月后,京津地区的反特监听台里突然又发现了另一种异常的电波讯号。
技术人员对截获的电波及时进行了分析,认定这是从京津地区某个国民党特务潜伏台发往台湾保密局的电报,并破译出该潜伏台的台长是由一个叫彭振北的人控制的,电文内容如下:
宋时轮部携苏式八十重型坦克喀秋莎火炮入朝。
反特监听台领导人将这一紧急情况立即汇报给了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杨部长再次将侦破潜伏台的任务交给了侦查科长曹纯之。
接到新任务的曹纯之从电讯组那里了解到,彭振北潜伏台极有可能与国民党原“保密局津源组”有关,于是立即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布置了对该组组长秦应麟的侦查工作。
曹纯之在侦查中发现,一个名叫“金太太”的女人曾与秦应麟有过交往。但这个女人是谁?住在哪里?与秦应麟是什么关系?侦查工作队的同志却一头雾水。
几天后,从河北公安局方面传来了消息说,秦应麟的事情又有了新的线索。
原来,这“保密局津源组”早在1946年就经常活动于津源、易县、定兴一带,为国民党长期提供共产党秘密情报。北京解放后,该组组长秦应麟在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副站长吴宗汉的布置下,将“保密局津源组”改为“建宛平潜伏组”,并领取了与“台湾国民政府”联系的电台后便不知所踪了。
河北公安局的消息还说,这秦应麟在北京是有家室的,而他的妻子就是化名为“金太太”的卞树兰。
公安部一局还从户口上查到原“津源组”成员胡振远的一些情况:
胡振远,男,25岁,河北雄县人,原住北京市西单保安寺18号。此人在北京解放后下落不明。
曹纯之得到了这些消息后,非常高兴,他与侦查小组的成员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后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从秦应麟的妻子卞树兰那里下手,引出秦应麟。
同年8月,侦查小组的同志们在家住北京道兹府10号南屋的卞树兰邮箱里发现了一封从天津寄来的信,经过鉴别,小组同志认为这封信极有可能是秦应麟发来的。
为此,曹纯之断定,秦应麟应该在天津出现过。他通知天津市公安局密切注意当地可疑人员的动向。
这时,侦查小组的同志提议立即密捕卞树兰,让她直接供出其丈夫的下落。但曹纯之却认为,天津寄来的信件没有具体的通讯地址,为避免打草惊蛇,还不能过早地惊动卞树兰,只能对其继续进行秘密监控。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卞树兰每天的活动正常。侦查小组的工作没有一点进展,同志们非常着急,曹纯之也眉头紧蹙。
又过了几天,电讯组那边传来了好消息,说电台获取了一份台湾保密局给彭振北潜伏台联系经费的电报,电文大意称:由香港派商人王永祥送来1000美元,到天津老太和药铺交卞树棠收转。
这份电报,给曹纯之和侦破小组的同志们提供了重要线索。他们通过调查得知,这电报中提到的“卞树棠”正是秦应麟的妻弟。
曹纯之立即指示部下将监控的对象由卞树兰转为卞树棠。
然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卞树棠却失踪了。
卞树棠的突然失踪,使这条线索在此断掉。曹纯之重新组织同志们召开紧急会议。经讨论,大家认为卞树棠是去了天津的老太和药铺。于是,再次和天津市公安局联系,将老太和药铺秘密地监视起来。
狡猾的卞树棠也许估计到了侦查小组的这一行动,几天过去了,他一直没在天津的老太和药铺附近露面。
为了不让他跑掉,曹纯之和天津市公安局的侦查人员分头行动,在天津布下了天罗地。
这天,在天津德华医院的门诊室内,走进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他双手抱着肚子,哭丧着脸,佝着腰,“哎哟”连声。看见医生,他连连要求住院治疗。
门诊医师见他痛苦的样子,随便地检查了一下,就让他填写住院单。只见他在住院单上的姓名栏里写下了“卞玉棠”,想了想,又在卞字上面加了一笔改为“卡玉棠”。护士接过他的住院单,叫了他的名字说:“卞玉棠,你跟我来……”他起初还应了一声,而后却改口称道:“哦!我,我不姓卞,姓卡。”
护士小姐疑惑地看了他一眼,将他紧张的神情就此记到了心中。
这天晚上,侦查小组的同志们来到了德华医院了解情况,在医院的会议室里,白天负责给“卡玉棠”带路的护士将自己的怀疑汇报给了侦查小组的同志们。通过辨认同志们获取的卞树棠照片,护士认定这“卡玉棠”和“卞树棠”正是同一个人。
于是,一条秘密的监视方案在曹纯之同志的脑海中形成。
第二天,“卡玉棠”的病房里又增加了一位新的“病人”,而这位“病人”就是曹纯之提出的秘密监视方案中的重要人员。
不久,秘密侦查员发现经常来医院看望“卡玉棠”的一个“药商”,极有可能就是这桩案件的重要人员。
根据这个情况,曹纯之从河北公安局发过来的资料中找到了证据,证明了此“药商”正是他们寻觅已久的“建宛平潜伏组”组长秦应麟。
曹纯之当即决定对秦应麟进行严密跟踪,但没想到,秦应麟异常狡猾,他在天津不停地更换住宿地点,给跟踪人员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8月22日,秦应麟从天津乘慢车前往北京丰台,到站后,他又在丰台买了一张去保定的车票。
当车到高碑店时,秦应麟突然下了车,跟踪的侦查员因人多拥挤,失去目标,一下子不知他的去向。侦查员立即请求河北省公安厅和保定公安处查找。
在寻找秦应麟的同时,医院这边也在密切地监视着卞树棠的行动。
这天傍晚,在一家大饭店里,卞树棠与香港的一名客商频频举杯,很快谈成一笔生意。那客商名片上写的姓名是“王永祥”,只见他打开皮包,交给了卞树棠一张银行的汇票。
三天后,侦查人员又发现天津市德康药房的李某给卞树棠送来了一大包人民币。
卞树棠收下钱,就收拾东西准备出院。
他的同房“病友”也随即同他一起出来,并殷勤地叫了一辆车,说是同路回家,但卞树棠马上就感觉不对,因为他们坐的车子不久就开进了天津市某公安分局。
卞树棠被密捕后,气焰非常嚣张,他在分局看守所里大喊大叫着:“你们凭什么抓我?我可是守法公民!”
侦查科长曹纯之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就不要再狡辩了。你应该知道我们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老实跟我们配合才是你的明智选择!”
卞树棠依然大叫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是守法的平民百姓,你们共产党怎能随便抓人呢?”
为了让卞树棠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当天傍晚,杨奇清部长亲自从北京赶来。他听取了曹纯之等人的汇报后,决定组织同志们尽快抓住那个和卞树棠谈生意的“王永祥”,再从他那里找到突破口。
遵照杨部长的指示,曹纯之和手下立即行动,于当天晚上就将王永祥捉拿归案,并将他关押到卞树棠隔壁的房间。
卞树棠清楚地听到了侦查人员对王永祥的问话:
“姓名?”
“王永祥。”
“哪里人?”
“香港的。”
“到天津干什么来了?”
“做生意。”
“什么生意?”
“药材。”
“生意做成了吗?”
“还没,没有。”
“那你给卞树棠的汇票是怎么回事?”
“哦!那是……是,买,买药材的。”
“你不是说生意没做成吗?怎么还给他钱啊?”
“那,那是给他,预付的订金。”
“订金!真的是订金吗?你最好是想清楚再回答!”
“哦!不是,不是,那些钱是别人托我带给他的。”王永祥支吾着,头上冒出了大滴大滴的汗珠。
“真是别人托你带的?那么到底是谁?说!”侦查同志提高了声音。
“是,是一位姓潘的老板。”
“是台湾特务头子潘其武吗?”
“嗯,是的!哦,不是!不!”王永祥吓的一怔,惊恐地看着侦查人员。
“你最好老实交代,我们可是有人证物证的。”侦查人员厉声说着。
“啊!长官,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呀!我只是个生意人!什么也不知道呀!”
“哦!是真的吗?那么这是什么?”侦查人员把电讯组截取到的那份电文扔到了王永祥的面前,只见上面的“香港派商人王永祥”下面划出了重重的标记。
在铁的事实面前,王永祥不禁瘫倒在地,他大声地哀求着:“我交代,我交代,我只是被他们利用,只求长官开恩,放我回香港,我可是有家室的人啊!”
卞树棠贴着墙壁听完王永祥的交代,顿时像只泄了气的皮球,嘴里念叨着:“完啦,完啦!”
当晚,侦查同志没有再继续审问卞树棠,而他则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一早,卞树棠便向着房外大叫:“快来人呀!我要交代!”
从卞树棠的交代中,曹纯之等人了解到去医院看他的“药商”正是秦应麟,卞树棠还交代了秦应麟可能逃往的地点。
几天后,根据卞树棠的供词,侦查小组的同志们顺利地抓获了秦应麟。可是大家翻遍了秦应麟的住所,也没有发现“彭振北潜伏台”的下落。
侦查科长曹纯之再次对秦应麟进行了讯问。他一开始便单刀直入:“秦应麟,解放前你就是对我晋察冀革命根据地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老牌特务;解放后你又逃到台湾,受保密局派遣潜回大陆,重组特务组,你知罪吗?”
秦应麟一听老底被揭穿,顿时满头冒汗,扑通跪倒在地,连连磕头:“我交代,我交代……”
秦应麟交代了被派遣的经过及电台的下落:“台湾派出的计兆祥电台被你们的人侦破后,有一天,毛人凤突然把我叫去,对我说:‘听说你在1939年参加本局工作后成绩突出,北京也有家,天津还有掩护,你马上潜回北京重新组建宛平潜伏组。’毛人凤任命我为组长。他还说,计兆祥的电台被你们识破了,是因为他的经验不足才使你们钻了空子,这次用我这个老经验,要我分散隐蔽电台,以免被你们发现。当时我说我的报务员已经被捕,我不懂报务,重新回去潜伏有困难。毛人凤说,你在北平的关系多,走时你带个报务员,隐蔽起来,不做其他任何活动就万无一失了。他又指示我说,解放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北京有5架电台,情报局撤出北京时,把这5架电台都交给北京的张某掩护起来了,要我直接去那里找张某要一台就行了。回到北京后,我就去那里取了一台……”
曹纯之继续追问道:“那另外的4架电台还在吗?”
秦应麟老实回答:“如果没有转移的话,那4架电台都应该还在张某那里。”
第二天,曹纯之带领侦查小组的人顺利地收缴了剩下的4架电台。台湾保密局苦心经营的天津“建宛平潜伏组”,就这样尚未真正立住脚,便被我公安机关一网打尽。
▲本文摘自《降伏恶魔——新中国开国之初的反特斗争》,周丽霞编写,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作者:周丽霞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徐坚忠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