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档案】全增嘏(1903-1984),浙江绍兴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25年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2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天下月刊》(英文)编辑,中国公学、大同大学等教授。从1942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任主任,同时任图书馆馆长。1956年,复旦大学创办哲学系,他从外文系转到哲学系工作,历任逻辑学教研室主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等职。专于西方哲学及西方文学。著有《西洋哲学小史》、《不可知论批判》,译有狄更斯《艰难时世》,主编《西方哲学史》(上、下册)等。
在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在新旧更替的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诞生了一批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师,全增嘏正是其中之一。全增嘏,字纯伯,祖籍浙江绍兴,自幼随祖辈和父辈生活在贵州、上海等地。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是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的后裔。由于家学渊源,全增嘏从小就熟读传统经典,国学功底深厚。
在学术界,全增嘏以西方哲学专家和翻译家闻名,并被誉为“中国英语四大家之一”。但事实上,他对中国学术经典的研读丝毫不亚于西方学术经典。据他的学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黄颂杰回忆:“他在指导我们学习西方哲学时,常常引导我们注意学习中国哲学。他家中中国学术文化的藏书量远超过西方学术文化的藏书量。他的书桌案头、沙发椅子上,少不了随时阅读的中国古代典籍,去他家时第一眼看到的常常是他手中的古籍。”(黄颂杰,《全增嘏与西方哲学》)
全增嘏的西学启蒙也比同龄人要早。1916年,天资聪颖的他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那年他只有13岁。在那里,他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并接触到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和文化。他的同学里有后来同为哲学家的贺麟先生。据全增嘏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姚介厚回忆:“贺先生生前曾对我忆述,当时和他同班的全增嘏年龄虽小却聪慧好学,熟悉国学,有家学功底,且早就接触西学,英语能力强,是论辩好手。”
“五四”前后,内外交困的中国社会亟需救世良方,各种思潮各种主义同台博弈。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全增嘏受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影响很深,对西方的科学文化很是着迷。著名哲学家杜威、罗素访华的讲演,更加深了他对西方文明的印象,尤其启蒙了他对哲学的兴趣。“那时我就想用西方的科学文化来解决一些我们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觉得哲学尤其重要,因为哲学不只能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全增嘏,《谈谈如何学习西方哲学》)1923年,结束了在清华园7年的学习,20岁的全增嘏赴美攻读哲学。当年他乘坐的邮轮可谓“群星璀璨”,和他同船的有梁实秋、陈植、顾毓琇、吴景超、吴文藻等人。

1923年全增嘏先生赴美船上合影,第三排左三为全先生
在美国,全增嘏只待了五年。他先进斯坦福大学,仅仅用了二年就获得本科学位;而后,他又进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并修完博士学位课程,这前后也不过三年光阴。治学如此高效的理由,除了全增嘏过人的天赋之外,在姚介厚的回忆中也可以找到答案:“全先生曾说,在哈佛,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图书馆。他经常带个面包,在大学图书馆书库内辟有的小房中一待就是一天。他说这样可提高时间利用效率、方便读到许多好书。可见,全先生的丰沛学养是在勤奋求知中获有的。”即便身在美国最高学府,作为中国人的全增嘏也同样是鹤立鸡群——他曾担任哈佛大学辩论队队长,其深厚的英文造诣可见一斑。
1928年,全增嘏回到上海。那时的海归人才凤毛麟角,上海各大高校纷纷向他递出“橄榄枝”。他先后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英文等课程。20世纪30年代,随着远东格局的变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兴趣愈发浓厚。对于那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仅仅是把西方文化引进来,思考如何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打破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方“独语”的局面,也是他们的共同理想。于是,全增嘏的身影同样活跃在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他先后参与当时中国两部最具国际影响的英文学术期刊——《中国评论周报》和《天下月刊》的编辑工作。
其中,创刊于1935年的《天下月刊》是首份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面向世界发行的全英文刊物。其宗旨是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学人所理解的中西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当时,《天下月刊》编辑部集结了一大批留学英美名校的回国青年才俊。他们既有丰富的西方文化知识和优秀的语言能力,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们不同于五四时期知识界激烈反传统的态度,注重在历史特性基础上的文化再造。当时与全增嘏共事的有吴经熊、温源宁、林语堂、邵洵美、姚莘农、钱锺书等人,他们不仅是编辑,也是撰稿人。期间,全增嘏写下了大量诠释中国文化的英文文章。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此知之甚少。但据通读过这些文章的学者回忆,由于全先生学贯中西,英文写作水准一流,这些文章涵盖了中西文化的诸多面向,至今都可以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极佳读本。
1938年,《天下月刊》编辑部整体迁往香港,全增嘏也迁居香港,继续担任编辑,同时兼任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和香港大学讲师。由于战乱导致经费短缺,《天下月刊》被迫于1941年闭刊。但毫无疑问,这本刊物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如有学者这样评价,“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都力图学习西方的文化来促进古老民族的崛起与革新,但《天下》编者和作者却以更为广阔博大的文化胸襟与更为神圣的文化使命感,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黄芳,《试论英文杂志〈天下月刊〉的文化价值》)
1942年,全增嘏回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外文系执教、并任系主任,至1956年转入哲学系,历时长达14年。期间,他对外国文学尤为关注,特别是对狄更斯的小说情有独钟。他与他的夫人、中文系胡文淑教授共同翻译了狄更斯的《艰难时世》,这是狄更斯小说中哲理最强也最难译的著作。这本译作问世后深受读者喜爱,被视为文学翻译界的典范。不仅如此,全增嘏还对狄更斯小说创作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由于狄更斯的小说以英国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为背景,揭露了统治者资产阶级的虚伪和受压迫者无产阶级的苦难,英美资产阶级学者对其颇有微词。而他在熟读狄更斯的全部小说,并融会贯通西方学者对狄更斯的评论,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狄更斯的看法后,写下万字长文《读狄更斯》,对这本小说给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这篇文字至今仍是狄更斯研究中的经典之作。尽管全增嘏后来以西方哲学专长,但他深厚的外国文学造诣,仍在学术界盛名远播。(黄颂杰,《全增嘏与西方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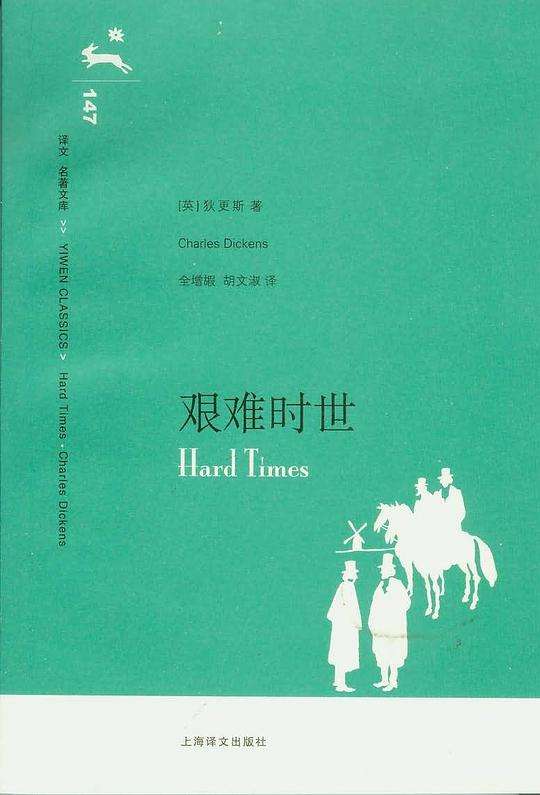
《艰难时世》
开中国现代西方哲学教学之先河
在哲学领域,全增嘏是我国建立学位制度以来全国第一批、也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一位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授。尽管全增嘏留下的哲学著述不多,无法全面展现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但这无损于他在国内哲学界的地位和声望,他在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等研究领域都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全增嘏就出版了他首本论著《西洋哲学小史》,这是最早的由我国学者撰写的西方哲学史著作之一。和许多大部头的西方哲学史著作相比,这本不到五万字的小册子可能会显得有点“寒碜”。但是,用黄颂杰的话来说,“它把二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分期归派,提纲挈领,讲得清楚明白,了然于心。时至今日,谁要是记住了这不到五万字的‘小史’,他可以说是掌握了西方哲学的‘大要’。”全增嘏自己在导言中也写道,这部“小史”仿佛是“点心”,目的只是在提起读者的胃口,因为是为一般人而写,所以尽量避免哲学家们用很多专有名词“叫人如坠五里雾中”的通病。“一本好的入门书是建立在作者对内容的全盘熟悉和融会贯通的基础上的。这本‘小史’很能看出全先生一生做学问、从事教学科研的特点:融会贯通,深入浅出。”黄颂杰这样说。
何谓哲学?这是学习哲学时一个最基本而又最不好回答的问题,在《西洋哲学小史》开篇,全增嘏借用美国哲学家霍金的定义——哲学是对信仰的批评,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他说,哲学是叫我们受智慧的指导而不要被偏见或权威所支配,因此其功用是在解放思想,是在改变武断的怪癖,是在保持人类的好奇心,使他们求知,以尽自己的天职。他将哲学分为三大类:对宇宙种种信仰的批评,形成宇宙论和本体论;对知识种种信仰的批评,形成知识论;对善恶、美丑等价值方面种种信仰的批评,形成价值论(包括伦理学和美学)。
在这样的哲学观指导下,全增嘏主张当把哲学研究的范围理解得宽泛些,除了宇宙论、知识论,还应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法律哲学、文化哲学,因而学习哲学的同时也要适当学习一些历史、文学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知识。在黄颂杰看来,这个主张是合乎20世纪初以来现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的,也与中国哲学的实际相符合。对于从古到今的哲学发展史,全增嘏也从不偏废哪一段。姚介厚曾将他的治学思想概括为“贯通古今,古为今用”,在他那里,西方哲学史是前后继承与变革、交叠互为影响的有机思想整体。其中,他特别强调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之根,和后来的西方哲学有割不断的源流关系,不了解古希腊哲学,对后世哲学的研究也就不易深入。据学生们回忆,他非常爱读柏拉图对话,并收藏了好几个英译本版本供学生研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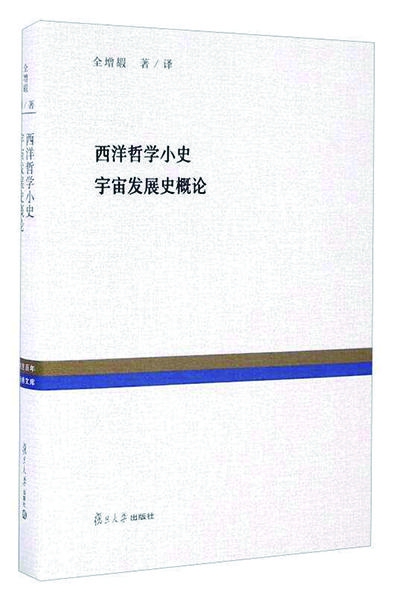
《西洋哲学小史 | 宇宙发展史概论》
全增嘏贯通古今,现代西方哲学是他一生追踪研究的重点领域。这也许与他在哈佛的求学经历有关——20年代初,英美哲学界掀起了一股“反唯心主义”而主张“新实在主义”的热潮,在全增嘏留学期间,“新实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哲学家怀特海也正好在哈佛大学任教职。在《西洋哲学小史》中,全增嘏就专列一章论述现代西方哲学。后来,他也一直想写一本专门介绍现代西方哲学的著作,由于抗战爆发而最终未能如愿。
1956年,复旦大学哲学系成立,时为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的全增嘏转到哲学系,担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和逻辑学教研室主任。1961年,全增嘏以“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在哲学系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系统讲述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这在当时的高校是绝无仅有的“首创”。这门课程后来在全国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由此奠定了复旦大学西方哲学研究的基础。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黑格尔之后的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是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时代,是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激变动荡的历史时期,而哲学正是了解这段人类认识进程一面极好的镜子。但在当时,讲授现代西方哲学需要很大的学术勇气,它被公认为是帝国主义反动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是政治上的“禁区”。并且,从学术上看,要将黑格尔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加以梳理,进行评论,使之系统化为一门学科,也绝非易事。(黄颂杰,《全增嘏与西方哲学》)
但全增嘏仍然坚守着他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给学生授课的同时,全增嘏还深入钻研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及存在主义,并发表一系列颇有深度的学术论文,这些领域在当时都是学者们不太敢涉足的。这一时期,哲学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被阶级化、政治化,全增嘏的学术研究自然也难以摆脱这方面的影响,但即便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他也依然坚持从西方哲学概念术语、命题主张的实际含义进行分析批判,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哲学家建立自己的体系总是有一定的依据,总是有它自己的‘理’,自己的逻辑。要根据这些去看看它们是否充分有理、是否自圆其说,才能做到科学分析,以理服人,不能先设定几条框框,然后到哲学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结果往往产生片面性,甚至曲解原意。”(全增嘏,《谈谈如何学习西方哲学》)
20世纪60年代,受当时的高教部邀请,全增嘏开始整理写作西方哲学史讲稿,原拟作为全国哲学系西方哲学史通用教材出版,在“文革”开始前已全部撰写完毕,可惜在“文革”中全部遗失。“拨乱反正”之后,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解禁。70年代末,复旦哲学系成立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全增嘏兼任该研究室首任主任,他继续致力于主编《西方哲学史》。80年代初,《西方哲学史》问世并获全国教材优秀奖,在学术界影响深远。复旦哲学系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也很快取得领先优势,全增嘏所发挥的奠基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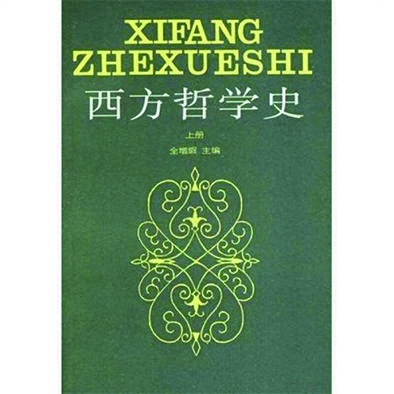
《西方哲学史》
培养学生是“手工作坊”式的精工细作
对于自己的学生,全增嘏倾注了全部的心血。1962年,教育部正式实施研究生报考录取制度,黄颂杰和姚介厚两人成为他第一次正式招收的西方哲学研究生。从那时起,全增嘏家的起居室就是学生的课堂,他的夫人胡文淑先生对此毫无怨言,反而每次都热情招待。有次她开玩笑说:“你们这倒像是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精工细作啊!”全增嘏回应说:“就应该这样学才学得好嘛!”(黄颂杰,《百年复旦哲学园地的园丁》)
在西方哲学的专业学习上,全增嘏教导学生首先要读懂读透哲学家的原著,强调阅读中要开动脑筋,有自己的心得、见识,不能让书中的“金戈铁马”在脑海中奔驶一番,什么都不留下;他要求学生每个月都要交一篇读书心得或文章,并且细致地评点与批改;他常说写文章切忌空泛发议论,务必言之有物、言之有据,他说做科研要像海绵善于吸水又能放水。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专题时,他特意安排学生去华东师大徐怀启先生(娴熟希腊文、拉丁文)家登门求教。他还多次带学生去南昌路上海科学会堂,参加上海哲学学会有关西方哲学的活动。由于全增嘏曾担任过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对图书资料很熟,他常常为学生准备好学习的图书,有的是他从图书馆借的,有的是他自己收藏的,这令学生们深受感动。(姚介厚,《从学治学沐师恩》)
在全增嘏看来,专业英语能力也是学好西方哲学的必备技能。姚介厚回忆说:“记得第一次去先生家里求教,他拿出一本英文书指定其中有关古希腊哲学的段落要我们立即笔译出来,他当场审改译文。他关注我们上研究生公共英语课,期末口试时这位原外文系主任竟也突然临场听考,外文系的主考老师和我们两名学生都甚为感动又有点紧张,幸好得高分没考砸。他亲自培训我们的专业英语,方式就是指定英文原著中某部分让我们当场口译,他给予校正,一并训练了阅读理解与口译能力。我当本科生时学俄语,仅靠看英语读物维系中学英语老底子,专业英语能力是在全先生指导下培养的,这对我后来治学和参与各种国际学术交往都甚有益处。”
在治学态度上,全增嘏要求学生必须严谨、踏实,切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他本人便是最好的榜样。据学生们回忆,“他讲课总有准备充分的讲稿,听他的课就是记一篇完整的文章。他写论文更是精益求精,层层剖析、逻辑性强。他和夫人合译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往往为获一最佳中译词而争论不休。”哪怕翻译的书出版后,他还要反复仔细校看并修改。“文革”后期,他被安排到 “自然科学哲学翻译组”,和物理系王福山教授翻译了好几本高难度的名著,如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梅森的《科学史》等。70年代末,一次和学生谈起《科学史》,他说即便已经前前后后看了20多遍,书出版后也还是不太满意。正如黄颂杰所说,“全先生满肚子的学问,可是他不动声色,不愿意流露。他讨厌卖弄学问,炫耀自夸,也反对读书求快而不求甚解,更反对不懂装懂。这是他们那一辈许多学者共同的特点,不过在全先生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和典型。” (黄颂杰,《百年复旦哲学园地的园丁》)
“文革”中,学生们原定的毕业论文选题不得已“转向”,全增嘏的研究生教育被当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文革”结束后,全增嘏的身体每况愈下,加之夫人在“文革”中离世的心理打击,还未将他深厚的学识发挥出来,还未来得及指导新进的博士研究生,全增嘏便于1984年与世长辞。
然而,那段追随老师学习的不长的光阴,还是在黄颂杰和姚介厚身上留下了终生的烙印。正是起步于老师的启迪,姚介厚后来回归古希腊哲学,将其作为自己毕生的重点研究方向。在2005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的后记中,他动情地写道:“年迈花甲,终于完成此书写作时,心中不禁涌起缅怀导师全增嘏教授的感恩之情……先师仙逝已逾20年,此书虽非硕果,也是献给他的一瓣心香。”而对于复旦西方哲学学科这块园地,全增嘏当年播下并辛勤浇灌的种子,也早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如今,这里已然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部分照片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提供)

作者:陈瑜
编辑:陈瑜
责任编辑:杨逸淇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