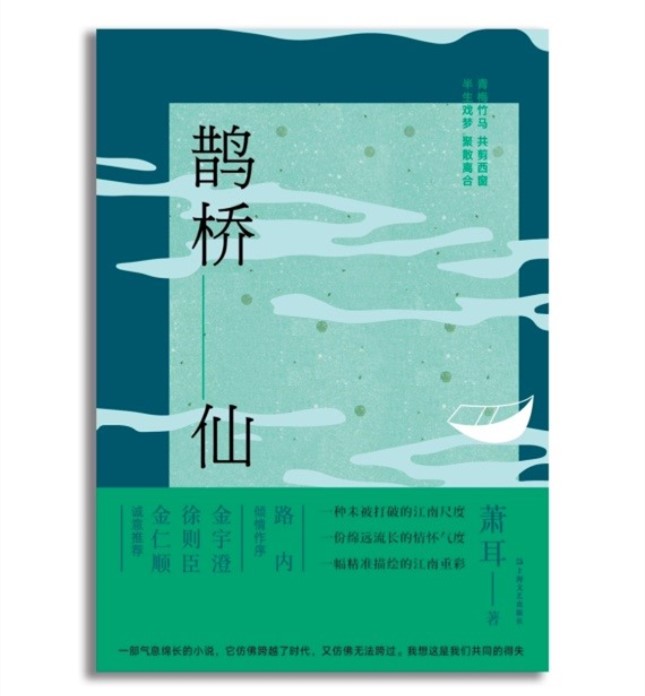
《鹊桥仙》
萧 耳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鹊桥仙》是杭州作家萧耳最新长篇小说,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1春卷》。小说追忆运河边的大码头——江南古镇栖镇的纷纭往事,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到新世纪,青梅竹马的一小群人,先后走出栖镇,此后各经人事,风筝的那根线仿佛要断,却又没有断……多年以后,看似繁华不再的江南古镇,再次成为昔日发小们的人生舞台。一场场婚礼与葬礼,一次次聚散离合之间,社会万象奔涌而来,亦可谓“往事成心事,流年似他年”。它被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金宇澄誉为——“给读者打开一幅精准的江南重彩图”。
>>内文选读:
沉 船
一九八七年,何易从和陈易知十八岁,身高分别是一米七二、一米六。戴正十九岁,身高一米六九。靳天十九岁,身高一米七七。这一年,栖镇这运河大码头似乎有点萧条下去的迹象。
处暑之日,何易从闲坐东横头家中,听到半导体收音机里,一段老生的昆曲唱腔,不觉入耳,一听之下,却有几分沉郁,原来是昆曲名家计镇华的《开眼上路》:春深离故家,叹衰年倦体,奔走天涯。一鞭行色,遥指剩水残霞。墙头嫩柳篱畔花。见古树枯藤栖暮鸦,叉桠。遍长途触目桑麻。江山如画,无限野草闲花。这是戏词。过几日要去省城上大学,易从望着河上船来船往,不觉又呆呆的,有点惆怅。
处暑前后,陈易知乘19路公共汽车去临平女同学刘春燕家白相,做了几日客。易知跟刘春燕告别,再乘19路回栖镇。下车后,过一号桥,照例又走东横头河边的小路,这条河边的小路,从东横头走到西横头,六年时光,从十二岁走到了十八岁,来来回回,走了上千遍。从何易从家门前路过,每次会朝他家里看一眼,看看他在不。从此以后,不会时常走了。
这次路过易从家时,他家的门关着。镇上住运河两岸的人家,白天有人时都不关门,邻舍隔壁,时常串来串去。那时民风淳朴,外来人口少,大白天关门是很奇怪的,你家白天神神秘秘,会被人背后戳脊梁骨。易知不知道,这一天易从也出门了,去了上海娘舅家小住。
八月的一些日子,考上大学的镇上发小们,打发暑假最后的轻松时光。吆五喝六,从这家屋里跑到那家,打牌跳舞,吃喝郊游,不亦乐乎。
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与考上大学准备出发的同学楚河汉界,听说已经有好几对谈起了恋爱,只有班花沈美枝凄凄惨惨,被男朋友高庆甩了,天天在家哭得梨花带雨。后来沈美枝气不过,叫了吉彪等几个男同学,把高庆和“财仙婆”打了一顿。后来又听说,沈美枝顶她妈的职,去了红旗丝厂。厂里青工白天上班,晚上经常一道跳舞,沈美枝成了舞会皇后。
“财仙婆”是镇上对妖媚不正经女青年的蔑称。沈美枝在其他女同学眼中,也属“财仙婆”一流,当然这里面也可能有嫉妒的成分。传说沈美枝高中还没毕业时,就时常逃课,跟社会上的男青年鬼混,时常被人看见在长桥上荡来荡去,压马路。这一次,沈美枝只是碰上了比她道行更高的“财仙婆”,“木郎”高庆被抢走,沈美枝无力回天。另一位美女杜秋依曾亲见过沈美枝在校园里抽泣,正好给上厕所回来的秋依撞见,原来是沈美枝在学校教学楼下走路的时候,被三楼吐下来的一口飞痰击中,那口痰正好落在她的秀发上,沈美枝恶心得哭了。据目击者说,吐痰的是另一个班的女生,也是个“财仙婆”,看中了高庆,因为看不惯沈美枝在高庆面前妖里妖气,就暗地里恶作剧出气。
消停了几个月,高庆看中的女子换成了煤球厂会计,一来二去好上,两人郎情妾意,蜜里调油,没料到后来女方却变卦了,看上了另一个在县城的干部子弟。干部子弟气宇轩昂,彬彬有礼地找高庆谈判,说女方已经不喜欢他了,还是和平分手的好。高庆黯然神伤,方知这男欢女爱的事,自己并非要风得风,要雨有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高庆不甘心,有一天厂里调休了半天,沉着脸走进煤球厂,穿过几个黑压压堆满黑色物体的车间,见到几个戴口罩的工人装煤卸煤,心情压抑。好不容易找到会计办公室,人家告诉他,那女子昨日请病假了,只得灰溜溜地回去。
这时沈美枝又回转来,对高庆百般示好。沈美枝每天下了班就去高庆家,高庆喝醉,美枝也陪他醉。高庆赶她走,她默默在一边不声不响。拉锯了三个月,高庆有点心软,有一天又喝醉,问美枝,枝姑娘,我对你凶巴巴,又三心二意,你为啥还这样对我,我也不是铁石心肠,也觉得对不住你的。美枝委委屈屈讲,我读初中时,有一回,跟我姆妈去栖镇剧院看戏文,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也不知哪里来的剧团,戏文结束时,我看到边上坐的就是你,眼圈有点红,好像流过眼泪,我印象特别深,后来学校里看到你,才晓得你是我们高年级的,教室在我楼上,后来我就老是注意你。高庆说,不会吧?我看戏文流眼泪?讲笑话。美枝低头垂目,不吭声。高庆说,我想起来了,确实是去看过这个戏文的,我那天一个人去的。沈美枝说,当时我也看得眼泪汪汪的,后来才晓得你是高庆。高庆嘴上说沈美枝是琼瑶看多了,心里却被打动。
心灰意冷间,高庆答应跟美枝结婚。十月,陈易知、杜秋依、戴正和靳天,都去吃了高庆和沈美枝的喜酒,高庆和沈美枝亲戚朋友都多,喜宴共办了五十桌。大婚那日,沈美枝的嫁妆,从水北绕一个大圈,一船花花绿绿的嫁妆从船上款款运来,陪嫁丝绵被就有十几床,登岸再走一段路,到了高庆家,高庆的苏州姆妈拿出压箱底的金货,项链手镯戒指全套行头,送给了新媳妇美枝。又拿出压箱底的绣花苏缎,给美枝做新衣裳。苏州姆妈性子耐,手巧,会做裁缝,美枝喜酒上要穿的一套中式衣裳,伊亲手给美枝量体裁衣,衣裳做好,美枝试穿,好看得像是从老底子香港电影里走出来。结婚那日,美枝新烫了头发,新郎官也是风度翩翩,气宇轩昂。这是栖镇大大小小的工厂工人阶级最后的风光了。
关于栖镇美人,这一届的镇上高中生中有个说法:沈美枝和杜秋依谁是第一美人?男生偏向认为杜秋依最美,女生普遍认为沈美枝最美。为什么男生女生会有这种认知偏差?谁也回答不了。共同的是,沈美枝和杜秋依都与大学无缘。
这夏日喧嚣中,陈易知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聚会,一次也没有撞上过何易从。
一日半夜,运河上乒乒乓乓,发出船只相撞的响声,几条大船上人声嘈杂,一会儿又听见河上汽笛声大作。船上喇叭叽叽呱呱通告事故的声音,易知在楼上睡着了,听不大真切,只是觉得这一天的夏夜,河上特别吵闹,到后半夜才昏沉睡去,居然梦到何易从站在一只水泥机舨船上,从她家门前河港过,又过了长桥桥洞,要往北面去。第二天清早醒来,易知开了木花窗,朝桥那头张望,才发现一只水泥船一半沉没,一半搁浅,占领了七孔长桥下一个桥洞的航道,船上的人早不见踪影,应该是转移到别的船上去了。
清早五点多,环卫所的装粪船按时停靠河埠头。易知起来,帮孃孃将马桶拎下楼梯,放到家门口,再上楼补个回笼觉。等环卫工人收拾后,又帮孃孃去河边刷了马桶。上午闲着无事,又用火钳钳了些刨花,点燃了煤饼,帮孃孃发好煤炉,烧好开水。这时候,孃孃喝的还是运河水,水装在大水缸里,用明矾过滤几日后饮用。离公用自来水龙头近的人家,已经开始用自来水。
易知孃孃在老房子门前嘀咕,罪过的,罪过的。我活着,不要看到桥撞塌掉就好了。
镇志上讲,大清同治年间,京杭大运河上才有了第一艘运货轮船。到光绪二十三年,有了小客轮,从此江南人可以坐小客轮去北方,北方人也可以坐轮船,沿着运河下江南,过长江,无锡、苏州、上海、湖州、嘉兴、杭州,都是真正江南好地方。

这日一早,栖镇航运部门,就在桥墩周围围起了警戒线,过往船只少了两条通行的航道,行船变得拥挤。很多拖着十几条拖船的货轮,排着队,依次缓慢行进过桥洞。船从易知家门口,一直堵到了易从家门口,一两小时过去,行行停停。
街坊邻舍议论,昨日晚上有条船被撞沉了,还把长桥的一个桥墩,撞了个窟窿。戴正则跟何易从打赌,从同治年间到这日,这段河上沉过几条船?到底也都不知究竟。
前一晚,易从枕河而眠,也听到汽笛声半夜喧闹,又紧又密,不禁猜测,会不会有几只轮船的船老大喝了点酒,抢着过桥洞,打起架来了。听说运河上的船老大,晚上喝了点酒,夜里开轮船也会争强好胜,互相别苗头。有的船老大拜过师傅,学过点拳脚功夫,行走江湖以防不测,喝了酒火气大,血一往上涌,就一撑竿,靠拢了“敌船”,人跳到“敌船”上,喉长气急,双方扭打起来,个别的,听说过闹出人命。动了刀子、浑身是血的船老大,被自家船上的人抬上了岸,火急火燎送到栖镇卫生所抢救,已经断了气,闯祸的船见事情搞大,连忙趁乱跑船了。
喧闹声中,易从比平常晚一些进入了梦乡。那天睡了懒觉,一夜睡梦中,又做了些纷纷繁繁的梦。梦见桥,大河小河,河水泛滥,哗哗地流,变成了海,他乘一只不大不小的船在海上漂,没有尽头,海上风大,把他身上的白衬衫吹破了,冷飕飕的,海面上一艘船也没有,后来大雾中看到一座小岛,却怎么也靠不了岸。岛上雾蒙蒙的,有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同学站在岛上向他挥手,头发长长的,一时想不起是谁。易从靠不了岸,更加怅然若失。正慌张时,忽有一白衣飘飘的少女,已跟他在一条独木舟上,软语温存,半张脸头发遮着,他们就亲吻起来,亲吻的感觉非常逼真,可白衣少女的脸却模糊,认不清是谁。
日高三尺时,易从被轮船汽笛声吵醒,才发现春梦留痕。不禁回旋梦中情事,又被电风扇吹得鼻塞,易从头昏昏然,开始流清涕。母亲喊他下楼吃早饭,桌上摆着豆浆油条,一只水煮鸡蛋,易从没胃口,吃一点就放下。母亲数落他吃得少,从小吃饭,食量像只麻雀一样,平时大鱼大肉不太碰,男小人身体发育阶段,炖小公鸡给他,也不肯好好吃,怪不得连一百斤重都不到。易从慢吞吞吃咸豆浆,不响。母亲又数落,你害我被人家讲闲话,女儿夭折,一个独养儿子养得皮包骨头。易从低头不响。
母亲走开一下,易从坐在桌边看一份新到的《参考消息》,看到世界人口达到五十亿。母亲回来,收拾碗筷,仍数落他吃得精刁。易从就讲,我不过五十亿人之一,渺小得很,胖点瘦点,有啥所谓。母亲白他一眼,说,不晓得你脑子里整天想什么。
母亲出门买菜,易从懒懒走上木梯,穿过走廊到自己房间,走到朝向河的一排木花窗前,看到长桥桥洞下斜歪着的水泥沉船,心里闪过一丝奇怪的念头:长桥下的船沉了,这是一个坏兆头么?
立秋已过,天气时有雷阵雨,闷湿难熬。易从这一场感冒又拖延了几日,人有点恹恹的,靳天戴正来叫过,也不太想出门,宁愿自己独处,错过了几场假日小聚。夜里着凉,白天精神不振,偏又不肯昏睡养身,歪在床上,反复读家中的一本有点破的旧词集《花间集》。从那年无意中拾得范小姐的小楷诗词残简起,易从就喜欢独自琢磨古典诗词,似乎很多诗词短句,正合着少年心绪。这几日因感冒而英雄气短,只有《花间集》销魂。
易从读到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好像说的是昨夜深宵的自己。读到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时,想起昨夜梦中模糊不清的少女,隐隐作痛。读到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又想起宝玉戏黛玉,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惹得黛玉生气,又平添惆怅。读到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又有书生知己之感。读到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明明人在家中,忽起莫名乡愁。感冒使人感官迟钝,但易从仿佛见自己的病魂在《花间集》中游走,通体透明,变得很轻。
病体初愈日,母亲喊他去对岸买米。长桥东边有两处轮渡,镇上人叫东摆渡和西摆渡。易从上了家门口的东轮渡,到水北米行买米,再坐轮渡,背着米回来。摆渡船上,碰到陈易知。见易知意气风发,那日穿着红点白底的丝绸连衣裙,在轮渡甲板上迎风而立,裙摆吹起,轻灵秀丽,易从忙和易知打招呼。易知问,长远不见,你怎么瘦了呀。不料正说中易从自卑心事,易从尬道,我吃什么都不长肉。易知说,是高考用功过度了。易从说,也没有,我们栖镇中学,不像你们临平中学学风好。易知未曾察觉易从被她说瘦而情绪低落,自顾自讲起昨日夜里,很多同学一道,刘春燕也来了,后来去我家聚餐,杜秋依也来了,说是给大家送行,后来又一起去镇政府团委办的舞会。闹到将近夜里十二点多才散场。
易从说,昨日这么多人呀。易知说,我们让靳天和戴正去叫你的,你怎么不来?易从说,不巧我感冒发烧了好几日。易知说,最后的疯狂,马上大家各奔东西了。易从说,真是遗憾了。易知又说,昨日靳天喝醉了,可能没考好,心里不痛快。易从说,大意失荆州了。易知说,以后我们的学校挺近的。易从笑笑说,我们都在杭州。
摆渡船到了河中央,两个就没话了,都各自看河。易知见易从兴致不高,一时找不出话接下去,心里委屈。等摆渡船靠岸,陈易知和何易从跟着人群上岸,也没道别,一个往东,一个往西走了。
时间快到中午,河上的船上人家,在船尾开始生火做饭,船尾是女人的天地,她们在操持着船上之家,洗米洗菜,下锅炒菜,小把戏们在母亲边上玩耍追逐,笑声很是响亮,一般总有两三个。因为行驶得慢,船上的生活,好像是水中央搭了舞台,嬉笑怒骂,一幕幕地在表演给岸上的人看。这是一九八七年的运河场景。
易知从西往东边看桥,长桥有点像老头,大船过桥洞,桥好像颤巍巍的,快要咳嗽出来了。易从从东往西边看桥,长桥有点像老妪,一脸深深浅浅的褶子,一双眼睛又好像随时要流出眼泪,曾经的河上佳人,早不是盛年模样。他们一年年看着桥与河,就一岁岁长大了,如今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
作者:萧 耳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