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人格——传统中国的阅读、注解与诠释》是一部探讨《诗经》解释的著作。作者深谙中国传统经典与文化,从《论语》《孟子》《左传》,以至《二程集》《朱子语类》等儒家典籍中寻绎出解释《诗经》的原则,从西方诠释学的视角探讨《诗经》学史上纷如聚讼的经典问题,如《诗序》之说、“六义”之旨等。在此过程中,作者不仅注重分析诠释者的处境、立场与关怀,而且关注诠释者与原作者共通的经验与情感。本书认为,诠释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质,塑造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也塑造了传统中国人对“人格”的独特认知。不同时代的诠释者在理解和解释《诗经》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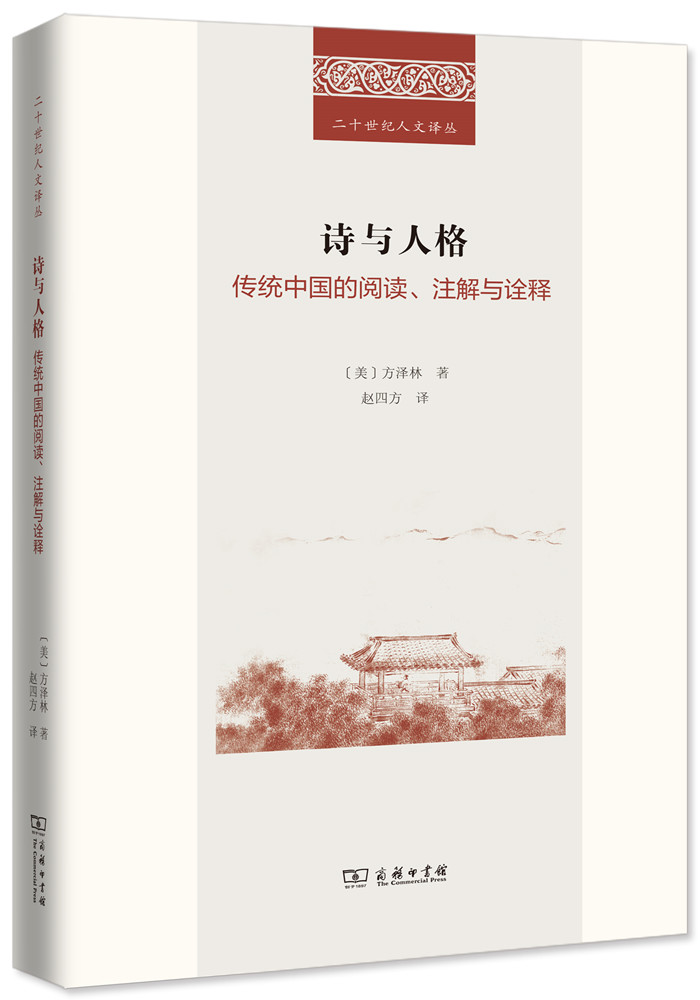
《诗与人格——传统中国的阅读、注解与诠释》
[美]方泽林 著
赵四方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文选读:
也有一些解诗的路径强调“志”的外部维度。在这一视角下,诗的创作与吟诵往往被理解为一位在下者向一位在上者的陈述——弃妇向其丈夫、臣子向其君主。在这种理解中,作诗者通过言“志”表达了意愿,而不顾这种做法将导致两个情人之间或君主与“道”之间不再和谐。出于不直陈意愿的得体或谨慎,这些“志”只能通过诗来间接表达。更概括地来说,诗就是“劝”统治者的“谏”,或者“美”,或者更为普遍的“刺”。作诗与诵诗(二者通常没有明确分界)的功能就在于劝说——通过对固有事物进行批评,或通过展示重塑了的社会样貌,诗可以感动和改变他人。
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作诗与诵诗的功能,有着深远的历史。在最初的运用中,诗通常与文字的神秘性——祷语、咒文和预言——紧密相连。在春秋与战国(前480—前222)时期,人们相信诗可以辅助“言”。这一观点不仅涉及诗的优美文句,而且涉及中国古人在音乐和诗歌中所发现的那种强大的劝说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们并不亚于古希腊人。(《左传》对诵诗与引诗的明显效用有大量的记述。)至迟在汉代,诗可以用来劝谏的观念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转折——诗的广泛流传被认为是帝国道德实现转变的优先手段之一。而且,诗不仅可以用来劝说他人,同时也用于说服自己。对它们的细密研究,尤其是记忆、吟诵、内化等,成为了儒者个人道德修养的核心要素。就像与它们相关联的音乐一样,诗在读诗者那里以一种特别直接的方式,感召最初作诗时的情感与冲动。因此,它们为感召情感的事业提供了一种优先手段,从而服务于儒家规范。诗成为了能够克服儒家传统中最棘手的难题的一种“超文本”(super-texts)。
尽管“诗言志”的观念可以有不同的侧重,并由此导致了理解《诗经》意思和意义的不同,但上述两种维度实际上是彼此关联的,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多被人们淡化,而并非强化。自我表露(Self-revelation)从来不是客观无情的,它总是在向一个人或一群人诉说,而不计会遭到多么强烈的否定。而且,在作诗或诵诗过程中所阐明的特定观点,总是被理解为具有社会和政治的后果。另外,人们认为恰恰是自我表露以及它在诗中留下的印迹,赋予了诗以特有的力量。
这一描述及与之相关的诠释学,在中国传统研究中发挥出极大的影响力。公元11、12世纪,宋代新儒家形成了有关经典的新的一般诠释学,而为其提供结构(如果不是词汇)的恰是诗的诠释学。而且,这种解释方法的影响并不限于经学领域。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假定,这些假定首先与诗有关,在“抒情诗”(lyric)的诗学中有所体现,它在公元1至3世纪时成为一种文学体裁。诗偶尔也出现——它产生于某些具体的、通常可指定的情形下,并且确实与那种情形“相关”。这也是自我表露,即诗人通过这种方法向同辈与后代子孙展现自己的人格特征,同时也展现自己并未与社会现实妥协的道德立场。因此,诗的理解通常是在了解诗人作为一个人的过程中达成的。最后,诗人的关怀通常被认为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关怀,他是以道德权威在言说。尽管这些假定在整个抒情诗传统中并不是统一的,但它们确实提供了作诗和读诗的基本语境。经过多次修改后,它们在视觉艺术和音乐的修辞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诗的解释史为我们考察中国的诠释学史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优势。在下文中,笔者将试图探究这一历史,或至少探究其中一部分。本书由两部分构成。接下来的四章内容探究了笔者所谓诗的“中古”理解的兴起与发展,它在《诗经》毛氏学尤其是《大序》中有具体展现。第二章为这种诠释学提供了汉代以前的背景,通过孔子的《论语》描述了诗的状况变化。第三章讨论与诗相关的特殊诠释学的起源。第四章重点关注《毛诗序》,尤其是《大序》。第五章探讨中古传统最具统摄力的硕果——《五经正义》。
作者:[美]方泽林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