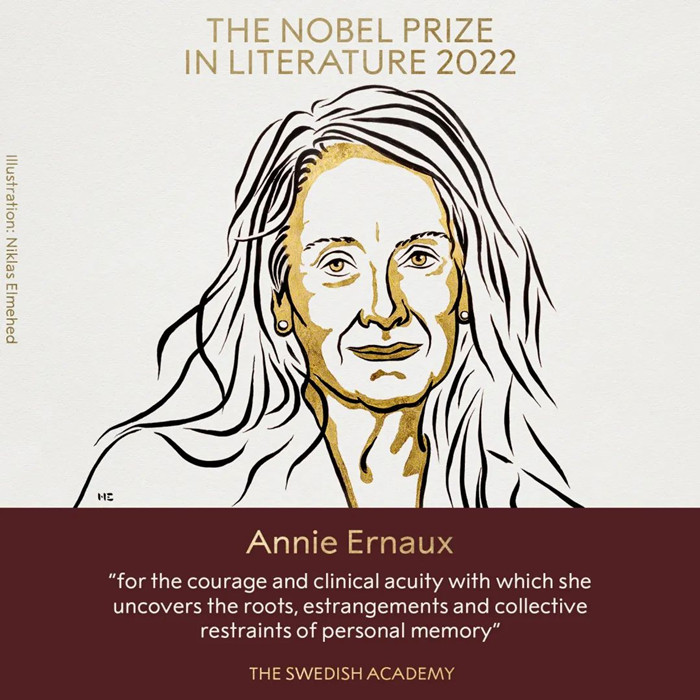
“她的勇气和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日前揭晓,82岁的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aux)摘得桂冠。
安妮·埃尔诺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十分熟悉,但在法国,她是最受关注的女作家之一。安妮·埃尔诺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在诺曼底的小城伊沃托度过童年。她起初在中学任教,后来在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退休后继续写作。埃尔诺从1974年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她共出版二十余种作品,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她的全部作品被授予“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奖”(2017年)、西班牙“福门托尔文学奖”(2019年)、“伍尔特欧洲文学奖”(2021)。她用细腻、伤感的笔触生动描绘了出身贫寒的父母如何为使自己及下一代摆脱社会最底层的卑贱地位所进行的充满失落、绝望、希冀、梦想的奋斗过程,准确、客观地再现了法国当代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心理、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差别,同时也以极其痛苦和矛盾的心情,真切表达了对父母及故乡爱恨交加。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2010年出版了埃尔诺的自传体小说《悠悠岁月》的中译本,这部杰作使她跻身法国当代第一流作家之列。而她的另外三本自传体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和《一个女孩的记忆》中译本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三本书的责编、上海人民出版社文化读物编辑中心主任赵伟表示,早在法国留学期间,他便读过埃尔诺的作品,出于对埃尔诺的喜爱,也出于出版人对于阅读市场的预见,他促成了这三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诺奖作品再次花落上海出版社,也体现了上海出版人的卓越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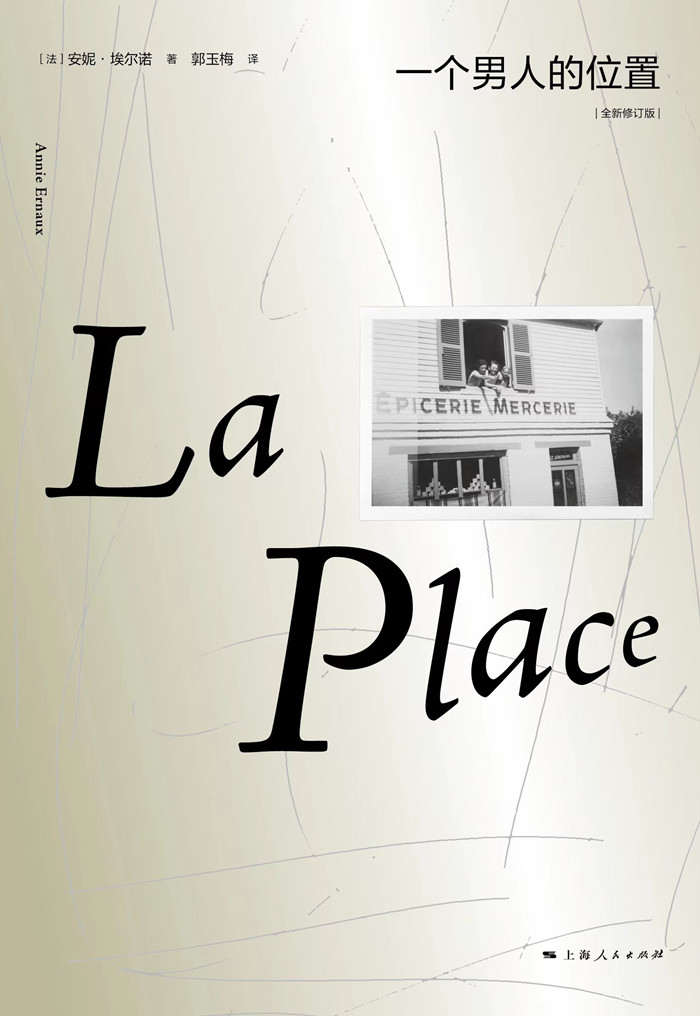
《一个男人的位置》(全新修订版)
[法]安妮·埃尔诺 著
郭玉梅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个男人的位置》曾获1984年法国勒诺多文学奖。在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两个月后父亲去世了,安妮·埃尔诺以此为契机,讲述了一个男人的一生。他出生于世纪之交,不得不早早离开学校,先是当农民,然后在工厂做工,后来成为诺曼底一家小杂货店的店主,直到1967年去世。他自我克制,勤奋工作,谨言慎行,努力维持着一个男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却始终无法摆脱对滑落回下层社会的恐惧。
作者用冷酷的观察揭示了困扰她父亲一生的耻辱,以及因阶层限制带来的父女之间的疏远和痛苦。这本父亲的传记也是一名知识分子女儿背叛的故事——背叛她的父母、她的成长环境,在亲情和耻辱之间,在归属和疏离之间的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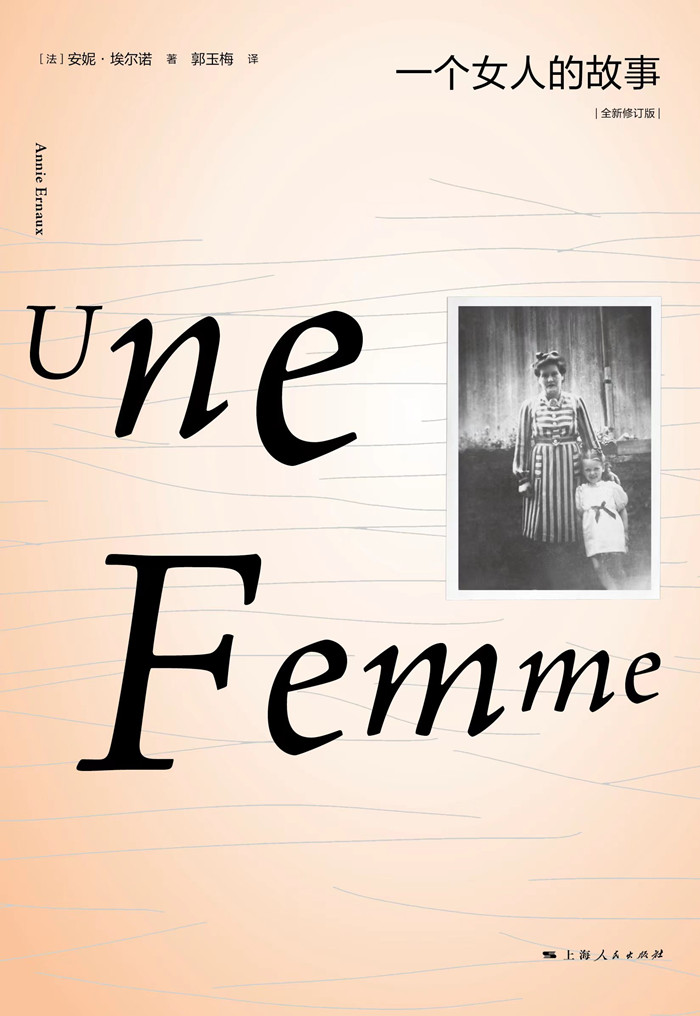
《一个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订版)
[法]安妮·埃尔诺 著
郭玉梅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个女人的故事》是安妮·埃尔诺对母亲和女儿、青春和衰老、梦想和现实的感人叙述。在母亲死于阿尔茨海默症后,作者开始了令人生畏的时光倒流之旅,她试图捕捉真正的女人,那个独立于女儿而存在的女人,那个出生在诺曼底小镇、死在巴黎郊区医院的老年病房里的女人。
她探讨了母亲和女儿之间既脆弱又不可动摇的纽带,将她们分开的疏远的世界,以及我们必须失去我们所爱之人这一无法逃避的事实。在这部平静而有力的致敬作品中,埃尔诺想要为她的母亲争取最大的公平:将她描绘成她自己。正如作者所说:“现在我写我的母亲,就像该轮到我重新让母亲出生。”

《一个女孩的记忆》
[法]安妮·埃尔诺 著
陈淑婷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一个女孩的记忆》这本书中,安妮·埃尔诺重温了1958年夏天在诺曼底担任夏令营辅导员的经历,并讲述了她与一个男人度过的初夜。当他移情别恋时,她意识到她已经把自己的意志交给了他,像是没有了主人的被征服者。六十年后的今天,作者发现自己可以抹去中间的岁月,重新回忆这个她曾想完全忘记的年轻女孩。将那个夏天不可磨灭的记忆带入现实,埃尔诺发现,她写作生涯的重要和痛苦的起源是建立在耻辱、暴力和背叛的基础之上。
正如安妮·埃尔诺所说:“生活并不能支配什么。它不会自己书写自己。它是沉默的、无形的。书写生活,就是要尽可能地接近现实,而不是发明或改造,就是要把它镌刻在形式里,镌刻在句子里,镌刻在词语里。”

>>内文选读:
追求“再现真实”与“内心流亡”的安妮·埃尔诺
——代译后记
郭玉梅
安妮·埃尔诺是当代法国文坛上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她以一个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和简洁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二战”后法国的平民生活,尤其是当代法国女性的内心世界。她独创了居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社会自传体裁,以平白中性的笔调书写个人的经历与社会的变迁。
自1974年第一部自传体小说《空衣橱》问世,安妮·埃尔诺至今已发表二十余部作品。她的小说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为代表的自传小说,另一类是以《单纯的激情》和《一个女孩的记忆》为代表的“私人日记”式小说。这些小说的发表每每引起轰动,读者蜂拥而至,先睹为快。自传体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在法国分别创造了50万和45万册的销量,引起了法国文学批评界的关注。其中,《一个男人的位置》荣获1984年勒诺多文学奖,并由此进入了大学的课堂,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
她的作品题材朴素,视角独特,笔调平实,体现了一种追求写实主义与心理描写相融合的风格,这在历经现代主义众多流派洗礼的20世纪法国文学中,既代表了某种回归传统,又体现了现代主义的某种升华。对此,虽然批评界尚有争议,褒贬不一,但这种独特风格至少已使她在法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她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一、坚持写实主义风格:追求“再现真实”
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省。她青年时代就读于鲁昂大学文学院和波尔多大学,获得现代文学教师资格。她幼年家境拮据。她的父亲阿尔封斯·杜塞斯原是一家农场的雇工,后又在工厂当工人,婚后与她的母亲布朗什·杜梅尼在一处贫穷的街区开了一家小咖啡馆兼杂货店,过着平民的生活。小说《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时期平民阶层的生存图景。
《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均属自传体小说。它们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女主人公,作品的“女性特征”可谓直截了当。
这两部小说分别讲述了出身贫寒的“我”与父亲、母亲之间既亲近又隔膜的复杂情感。她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中是这样说的:
“我要以我的父亲为主题,书写他的生活,书写我在青春期时与他之间的距离。虽然这种距离是一种阶级距离,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说的,就像爱的分离。”
小说以真实平实的笔触,记录了“我”在父母的期望与呵护下,在渐渐朝资产阶级阶层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内心世界和外在环境之间出现的不平衡。通过叙述“我”与父母亲逐渐产生隔膜的过程,写实性地再现了法国“二战”后时期下层百姓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
安妮·埃尔诺写道:
“我这里写的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某种东西。我的母亲出生在下层社会,她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世界里不觉得太孤独和虚假。”(《一个女人的故事》)
“我明白写小说是不可能的事,我只是要叙述一个为生存而奋斗一生的人,我没有权利将我写的作品称为艺术,更不能追求作品如如何令人激动。我只是要把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以及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事客观地记录下来。”(《一个男人的位置》)
从作者的上述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其作品中所追求的就是要用一种平实的语言记下社会历史真实的一幕。
这种写实风格一直是安妮·埃尔诺小说创作的指南。由于使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和女主人公合而为一,她在用她的视角解读、体验和描述世界,她的作品读起来似乎永远都是和她血肉相连的真实故事。其实我们不必去严格考证每个细节的真实性,我们更在意的是她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追求写实的风格。她拒绝某些同时代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法国人的生活图景,在她看来,那些故事对多数法国人来说是不真实的,更像是人们刻意杜撰出来的:
“当我读普鲁斯特或莫里亚克的作品时,我不认为他们写的是我父亲童年的那个时代,父亲的生活背景属于中世纪。” (《一个男人的位置》)
那么作者在其作品里给我们展示的真实情景又是怎样的呢? 她首先表现的是当时人们贫穷的社会生活状态:
“他们住在一间很矮的茅屋里,屋顶是用草盖成的,地面是泥土的。在扫地前,必须洒上水……人们总是提前几个月就会想到亲朋的婚礼或是领圣餐活动,他们带着空了三天的肚子参加,以便更好地享受机会。村里有一个患猩红热的小孩病情刚有所好转,由于大人拼命地给小孩往嘴里喂鸡肉,孩子在呕吐时呛死了。” (《一个男人的位置》)
由于贫穷,人就会信神:
“为了治好病,她常去参拜圣里基耶和圣纪尧姆,用一块布去擦拭圣像然后再裹在患处。渐渐地,她瘫痪了。他们租用了一辆马车,拉着她去参拜圣人。” (《一个男人的位置》)
由于贫穷,生存就会成为最大的命题:
“孩子们的肚子里总是有蛔虫。为了驱虫,人们就在他们的衬衣里面靠近肚脐的地方缝上一个装满大蒜的小袋子。冬天,在孩子们的耳朵里塞上棉花。” (《一个男人的位置》)
由于贫穷,人就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
“父亲害怕失去位置,害怕感到羞耻……一天,他在公证处办事,按要求他要在文件上第一个写下“已阅并同意”的字样,可他不会拼写,结果写下了“已阅并证明”。这种事情让他感到很尴尬,在回家的路上,这一错误让他翻来覆去地难受了一路。耻辱的阴影。” (《一个男人的位置》)
基于这样的生存条件,人们无非有两条出路:要么破罐破摔,自甘贫穷,要么通过不懈奋斗去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我”的父母选择了后者。他们先是改变了自己的雇农身份,进工厂做工,接着又从工人转成了小商人,小心谨慎地经营着自家的小店。接着,他们把自己最大的理想寄托在他们唯一的女儿“我”身上,他们节衣缩食也要把女儿送到当地最好的,只有有钱人才进得起的私立学校。
“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把这个‘希望我生活得比他们好’的理想取代了他们自己的理想。” (《一个男人的位置》)
艰难的生存条件促使父母下定决心,要把女儿朝着资产阶级方向培养,这成了他们年年月月悬在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女儿得到奖学金,去国外留学,被周围所有的人羡慕,这一切使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欣赏和仰视,而同时为自己平民身份更加感到自卑。
对生活的这种体验之细腻和审视之深刻显然来源于安妮·埃尔诺自己的身世和经历。显然,作家熟悉平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了解下层平民共有的社会心理特征,并且懂得如何从人们的生存环境出发去解读个人心理活动,并揭示其社会动因。她首先注重的是社会的人,她竭力表现的是个人心理活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逻辑。我们看到,由于作者既有感性的生活又有理性的分析,所以她的作品更具有真实性、典型性,这或许是许多作家所不具备的。再加上作者的女性视角,更使这些作品带上了特定的性别色彩,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长期以来,女性写作常常受到由男性主导的批评界的歧视,被贬为“自我中心主义”。诚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安妮·埃尔诺的女性自传体小说创作书写的大多是个体的感受,讲述的是女性人物自己的故事,但同时,她的叙述也涵盖了一般社会意义上的个人和群体。在她的作品里,个人和社会的维度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运用个人的故事去理解和展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这种手法拓展了传统女性文学狭隘的视野。特别是作者把握了女性私人故事与社会历史张力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审美内涵,体现了一种具有现实主义深度的女性文学的美学价值。换言之,她的作品不再仅仅是个别女人生活的实录,而是成为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
由此可见,她的这种写实风格体现了法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在回归传统的同时,我们还会发现,她在心理描写方面也吸收了某些现代主义的元素。
二、女性视角下的心理描写:解析“内心的流亡”
安妮·埃尔诺作品的主题大多建立在女主人公的私人生活之上,涉及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和她自己的爱情,属于“私人叙事”一类,其中表现最多的莫过于展现女主人公的情绪、体验和心路历程。因此,安妮·埃尔诺的这种女性视角下的心理描写就成了其作品的一大特色。
安妮·埃尔诺笔下的女主人公出身卑微,但天资聪颖。她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在私立学校里学习优秀。但她的思想也由简单开始变得复杂。换句话说,“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家庭的社会地位的卑微。在与同学交往的过程中,如果有同学要来她家里玩,她总是要事先对同学声明:“你知道吗,我们家很简陋。”即便是“我”结婚后,在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丈夫家里,这种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依然挥之不去。
“在他(丈夫)的家庭里,比如说,如果打碎了一只杯子,有人立刻就会喊道:‘不要去碰它,因为它已经碎了’。”(《一个男人的位置》)
对于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层的“我”来说,与父母的那份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是生她养她的父母,是希望她“生活得比自己更好”的亲人;而另一方面则是这亲人之间不再有的心心相印的理解,在心灵上的无法沟通,因此,“我”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痛苦之中,那是一种深隐于内心的痛苦,是一种心灵的煎熬,“我”把这叫作“内心的流亡”。
女主人公内心的矛盾来源于她同时生活于两个阶层。她在平民阶层里长大,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同时她又跳出了出身阶层的桎梏,迈入了一个更高的阶层,然后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俯瞰她所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而作者要解析清楚这“内心的流亡”,则完全有赖于细腻的心理描写。
我们不难发现,在女主人公讲述的故事中,写实的叙述与心理描写已经相辅相成,融为一体。这里,我们试从小说叙述形式的角度来分析安妮·埃尔诺作品中的心理描写的主要特点。
首先,如前所述,其作品在叙述形式上全面采用了第一人称“我”的自传体叙述方式,叙述者和女主人公合而为一,直接用女性的眼睛和心灵看世界。 这样一来,作者就彻底避开了男性话语的笼罩,便于直接抒发女主人公自己的真情与体验,直接将她自己的情绪和心路历程展示出来。显然,从创作的角度看, 以“我”作为切入点,更有利于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复杂多变的情感、心绪和内心世界, 也更具有表露个人“私秘性”的便利之处。这虽然不是女性文学的一项专利,但却可算作以文学方式展现女性自我的一种有效的武器。
其次,其作品普遍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形式。例如:《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在追忆父亲母亲一生的多个瞬间时,叙述者常常把叙述往事的进程暂停下来,把读者从往事所处的“过去”拉回到她“写作时的现在”,详细讲述她在写作每个片段时的感受,发表一番议论。作者通过这种夹叙夹议的叙事方法,把过去的场景与“现在”的情感交织成一个特殊的时间图景,使追忆者(女主人公)通过“现在”这个维度去透视“过去”,使“过去”变得更加清晰,使意义与情感更加厚重。这样,作者很巧妙地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例如在这两部小说中,这种手法使女主人公“我”通过反思过去,获得了忏悔和自我疗伤的机会,使“我”流亡的心灵得到了一丝宁静。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使读者强烈地感到叙述者兼女主人公就是作者本人,感到故事是真人真事,从而更增加了真实感和感染力。其实,我们尽可相信作品中的“我”既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又不一定完全是她本人,因为我们这里要做的并不是发生学考证,而是对文本风格的美学批评与欣赏。
最后需要指出,两部小说的主题本身就使得心理描写成为题中之意。这些小说都是围绕女主人公的 “私人叙事”,其主题和话语反叛了传统作品喜好的宏大叙事, 倾注于边缘个体的感性体验,创建了一种当代文学的“私小说”模式。所以我们看到,在安妮·埃尔诺的笔下,女主人公每每面对着矛盾而无奈的世界,只能逃逸到自己的心理世界之中,选择内心的流亡。
三、简洁与朴实无华的语言
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大都短小精悍。纵观两部小说,它们都是以日常生活为基本题材。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波澜起伏的复杂故事情节,看不到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描写,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对日常琐事的回忆。但作者却运用清新简约的语言娓娓道来,把一个个平淡而又充满生活气息和生命活力的细节展示在读者面前,将生活的平常与真实贴切地表达出来。
安妮·埃尔诺的小说大多采用平淡的叙事语气。她尽量将自己的情感压抑在如同潺潺流水般的述说之下,让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地展露,让生活的本色呈现出来。例如:
“父亲在咖啡馆里、在家里时很喜欢聊天,可在那些法语讲得很标准的人面前,他就会一声不响,保持缄默,或是话说到一半停下来,伴着手势说:“是不是?”或者简单地说“不是”,然后用手势示意对方接着替他说下去。父亲说话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唯恐说错一句话,会像当众放屁一样出丑。”(《一个男人的位置》)
在语言的运用上,安妮·埃尔诺用词之清淡是独树一帜的。她的作品语言自然,简洁流畅,朴实无华,不饰雕琢,然而实际上却是独具匠心。她从不使用冗长复杂的句子,多采用单部句、省文句,以及结构松散的日常口语句式,通俗易懂。她很少使用具有夸张色彩的形容词或修饰语,她认为只有白描的写作手法才是最精确的。她说:
“女性小说中近乎疯狂地使用那么多的形容词,如:傲慢的神态、阴郁的声音、傲慢的语调、嘲讽的口吻、尖刻的语气等,我想不出现实生活中我周围的人有哪一个可以被用上这样的词汇来修饰。我觉得我一直是在使用着这种当时很物质化的语言来写作,而不是用当时我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词汇来写作。我永远也不会体会到运用比喻方法的神奇以及运用文体修辞的喜悦。”(《耻辱》)
“我尽量地贴近我所听到的单词和句子,……而我之所以这样写,仅仅是因为这些词和句子说出了我父亲所生活过的、我也经历过的那个世界的限度和色彩。那是一个语言是现实的表达的世界。”(《一个男人的位置》)
当然,平淡不等于乏味。这需要作者极高的写作功力。这种写作风格,加强了作品厚重的现实感与真实感,透出了作者追求真实叙事的努力。
简洁清淡的语言已成为安妮·埃尔诺表达思想感情的最重要的方式,也构成了她的小说的美学特色。
文学批评界的有些人,认为她过于沉湎于普通人的生活。可安妮·埃尔诺则认为,为生活在平凡中的人们诠释真实才是艺术的最高命题。多年来,作者一直坚守着平民的立场和视角,抵制着以权力形态和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为主流的文化世界和空间。她说,“我背叛了传统的文学创作,即我在大学所学习过的那些创作规则”。她就是要通过书写那些类似超市、公交车、堕胎等这些被文学嗤之以鼻的“微不足道”的物和“凡人琐事”来颠覆文学和社会固有的等级。
谈到小说的形式,她认为,是有事要说才导致说话的形式。她从新小说那里得到的启发就是“写作是探索一种形式,而不是复制。”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她没有犹疑和惶惑,她称自己并没有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有的只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觉的真实抒发。只有把握自己的心灵自由这一基准,其作品才会有久远的存在价值。这也许是对其创作风格的最好诠释。
——本文摘选自《一个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订版)》
作者:安妮·埃尔诺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