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忧伤》是一个曾经的放牛娃、一个学了四年畜牧兽医专业的作家,与八种动物之间一桩桩生趣盎然的生命故事。这些动物和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有时候看似是动物,它却有着人的品质;有时候看似是人,他却有着动物的本性。人和动物永远难以划清界限,命运总是相互纠缠,所以要相互善待,彼此尊重。
《动物忧伤》的主角是猪、猫、鼠、羊、牛、狗、鸡、蛇。一方面,“我”对每种动物的记忆都是从故乡开始的,它们牵连着父母叔婶、儿时伙伴、熟人社会,对故乡的深情蕴含在家乡的山水草木中;另一方面,每种动物的归宿也都是在城市结束的,它们牵连着大都市新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生活习惯。有些看似闲笔,但“形散神不散”,有些虽是趣事,但能勾起人心中最深的情感,直抵灵魂,显示出质朴、悲悯、伤怀、温情和热爱的力量。
作为散文家、诗人的陈仓,文字以白描为主,语言幽默生动,具有节奏感和韵律美。他善于将平淡生活写出浓郁意味,简洁的文字中折射出圆熟的智慧。比如,作者笔下的老鼠,是在黑暗的夜晚,陪伴孤身在家的少年尽情玩乐的伙伴:它们为他跳舞,他给它们吃爆米花,一只小老鼠不小心踩了炉火上的铁锨,“抱头鼠窜”了。作者笔下的猫,野性而自由,在写猫与狗的不同时满是调侃的味道,而野猫作为另外一种存在,不接受人类的饲养,拥有自己的领地,独立而自由地生活在大自然中……
可以说,《动物万岁》选择了一个独特的主题,重新阐释了人与动物互相依存、扶持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情感的,也是社会的,既是对普通动物和人个体的命运剖解,也有对整个人与动物世界的关照。正如封面所说,动物们的一生,也许不过是我们自身命运的缩影。动物们的悲喜人生和人的命运交织,让人在荒诞中感觉悲伤,又从悲剧中触摸人心的暖,具有独特的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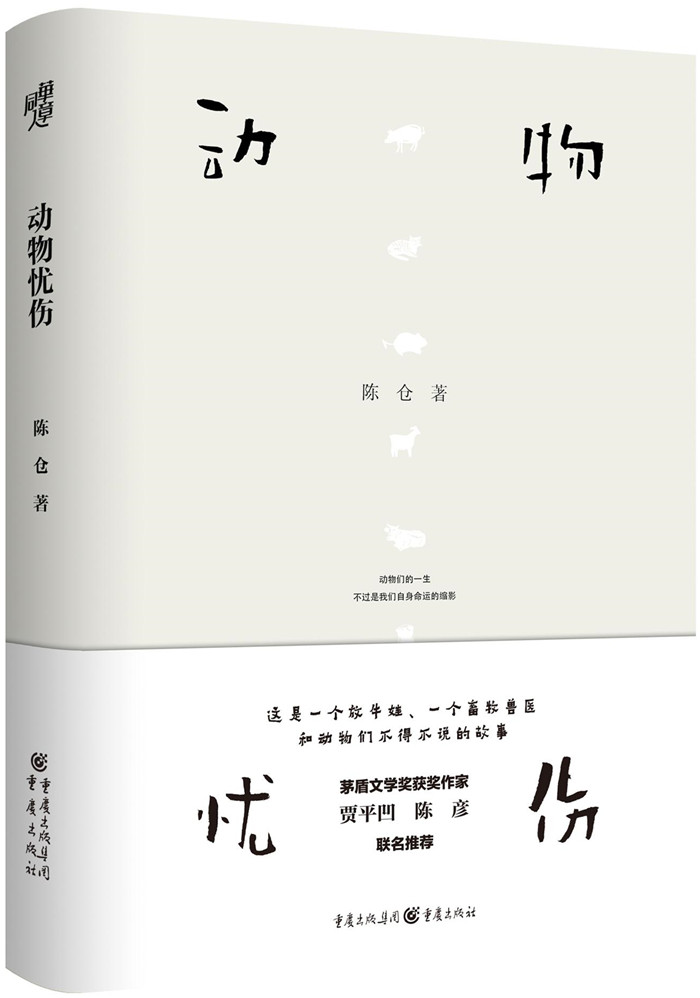
《动物忧伤》
陈 仓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
相关阅读
后记:人与动物共同的语言是爱
你创作《动物忧伤》(原题目为《动物万岁》,首发于《中国作家》2021年第4期)的灵感来源于哪里?
我是一个放牛娃出身,又学了四年畜牧兽医专业,而且我们家在秦岭南麓,过去自然环境比较好,狼、蛇、老鹰、麋鹿、獐子、野猪、锦鸡、果子狸,司空见惯,猪、牛、羊、鸡更不用说,几乎是同起同宿,所以从小就和动物打成一片。我写这本书绝对是天意,就在2020年春节前吧,福建搞了一个小说培训班,邀请我和文学朋友们交流,地点是闽北霞浦。这个小城令我心动的地方,主要是站在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看到寺庙,有时候很难分清楚到底是寺还是庙,即使躺在宾馆的床上也不例外,圣水寺呀,玉山寺呀,目莲寺呀,供奉什么的都有,除了常规的神佛以外,据说还有菇神和茶神,甚至是蛇神、狗神和鼠神……活动结束的那天半夜,当地的朋友选了一个大排档,请我们喝酒吃海鲜,大家喝着喝着,就聊到了药膳,由药膳聊到了中医。我说我是学医的,而且学的兽医,人哪里不舒服会说出来,但是动物不会说话,所以兽医比人医高明。为了不让大家看不起我,我就开始讲如何劁猪骟牛,听得大家目瞪口呆。大家纷纷说,这么有意思,你应该写出来。有人把书名都起好了,叫《我和畜生》,有人把广告语都想出来了,叫“我和畜生不得不说的故事”。
回到上海以后就是春节,由于我爸一直生病,而且隔三岔五地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他欠我了。“欠”是陕西当地方言,是想的最高境界。我就订了正月初一回家、初九返程的火车票,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新冠疫情暴发了。开始看到消息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在乎,年夜饭照订,各种各样的应酬照旧,因为非典期间,我正好在福建工作,那时候福建没有一个病例,我根本体会不到什么叫病毒,什么叫传染,什么叫隔离。直到出发前六七天,形势越来越严重,而且从老家传来消息,县城和村子之间的交通中断了,通往西安的班车也停开了。我想了想,就把火车票退掉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单位推迟上班,学生推迟开学,春节假期无限延长,每天都会涌现许多催人泪下的抗疫故事。
于是,从大年初一开始,我把晚上的五个小时时间,拿出来创作《动物忧伤》,可以说那些日子,不用操心上班,不用出门应酬,窗外也没有跳舞唱歌的干扰,除了为疫区的朋友们担心和帮忙购买口罩而想想办法以外,再也没有人间的任何烦恼了,真有些回到古代的那种感觉。疫情是无情的,但是对我个人的写作而言,真是人生当中少有的时光。所以,我写得非常顺利,到正式复工的时候,初稿已经写得差不多了。写完《动物忧伤》那天早晨,大概六点左右吧,我突然听到喳喳的叫声,这声音就站在窗外的空调上,和我离得太近了,仅仅隔着一块玻璃。它叫得太好了,主要是非常清脆,没有任何乐器能响得这么清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喜鹊,在上海十八年,在这栋房子里也住了十三年,原以为上海是没有这种鸟的,这种鸟只会生活在山里,生活在没有烟火气息的地方,和神仙以及我爸的生活环境非常一致。在陕西老家,喜鹊非常多,它们站在屋顶上喳喳一叫,每个人都心领神会,它是报喜来的。我非常奇怪,它们怎么知道我写完了这部书呢?难道它们真是上天的代言人?
你在《动物忧伤》中想表达的初衷是什么?
2020年春天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戳痛了我们的心。2003年发生非典,传言病毒来源于果子狸,现在的新冠肺炎病毒,有一种说法是来自于蝙蝠。我曾经拥有一杆长枪,是打鸡毛信子的,里边装着黑火药和滚珠,我经常背着枪上山打猎,朝着大树东瞄瞄,朝着白云西看看,虽然没有直接打死过一只猎物,但是跟随着舅舅和叔叔,打死过野猪、野鸡、獐子、果子狸,那时候这些东西还没有成为保护动物。所以,写《动物忧伤》,我是给自己的行为定罪来的,是接受大自然判决来的,是祈求那些被忽略被轻视被伤害的生命宽恕来的。
其实,任何一个生命,无论一只蚂蚁还是一只大象,无论一只麻雀还是一个人,在世界上活着的权利是平等的,有时候看似是一只动物,它却有着人的品质,有时候看似是一个人,他却有着动物的本性。人和动物永远是分不出高低的,划不清界限的,我们的命运总是相互纠缠的,所以要相互善待,要彼此尊重,唯有如此,灾难来还是不来,能够获救的都是有爱的灵魂。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动机,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起码是最真诚的、最有善意的作品。像找了一个对象,她不见得是最漂亮的,但是她对你是认真的,是想和你一起过日子的,这就足够了。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