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从文学到影视,关于历史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转向,更加注重用现代人的视角去打量和表现那些构成了历史微积分的芸芸众生,填补了历史叙事的缺口,展现另一番开阔天地。
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被呈现的?
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华东师范大学远读批评中心与孙甘露、张挺和黄志忠三位艺术家进行对话。其中孙甘露是著名作家、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近期新作《千里江山图》描绘了一个发生于1930年代的革命故事,该部长篇小说已进入影视改编的流程,曾获“五个一工程”奖等;张挺是著名导演、编剧,先后多次编剧、执导《大明风华》《天下长河》等历史题材电视剧,曾获白玉兰奖、夏衍文学奖等;黄志忠是著名演员,在二十多年的演艺生涯中,成功塑造了诸如《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立仁、《天下长河》中的靳辅等角色,并多次获白玉兰奖、飞天奖、金鹰奖等。
三位艺术家的影视和文学创作都力图呈现历史的复杂面向和精神结构,以各自的实践深刻地探讨了表演与人物、历史与影像、文学与现实等议题。

文汇报:一段时间以来,历史叙事的语法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什么?历史题材创作能持续吸引大众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认识历史叙事和历史之间的关系?
孙甘露:就拿《天下长河》讲述的“治黄”来说,黄河治理和漕运的关系给里沙河地区的人文地理、社会经济生活都带来了巨大影响,包括后来的自然灾害、流民这些历史上反复发生的事情,以及后世产生的民间艺术形式,都跟大的历史背景有关系。我们现在看到不仅仅是电视剧,包括历史写作也越来越多地从私人史的角度、物质史的角度、器物的角度来丰富和反观以前所谓的宏观的历史写作。有这么多细节来丰富的话,历史的真实面貌逐渐也就汇聚出来了。
当然,个人的历史讲述、私人的历史角度,包括影像的、图片的、日记的这些讲述非常重要,这些个人的、细微的、微观的讲述,好像是要从一种大的历史叙述当中挣脱出来的努力,但实际上也屈从于一种历史的意志。这个关系就是这样,实际上是很可玩味的。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历史剧或者说关于历史的这些讲述、艺术上的呈现,很多都是基于对当时历史时代的脱节的一种描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都是一些历史的命题。
张挺:个体意识的觉醒和情感体验的丰富,是现代历史剧的一个最新的变化。
早期的历史表达是有权威性的,有统一的表达方式,有史官的统一记录。而当我们谈论到历史中某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不是和我们经历一样的人生难题,体验一样的人生况味,这些都是个体性的认知。个体意识的觉醒促成了表达的变化。这不光是历史剧的问变化,而是所有戏剧的变化。

大家去重新关注历史剧,是因为历史剧提供了人生样本。我们可能没机会像靳辅这样活一生,也可能也不会像陈潢那样活一生,但是他们提供了不同的人生样本,让人在观看他们的时候,同样经历和感受到了那些东西。我们的人生体验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亲身体验,这种体验其实很少,另外一种审美体验,实际上就是通过观赏得到的,它增加了人生的丰富性。
具体到历史剧的创作,在哪个时期历史剧都不是创作频率最高的戏。你可以去做古装,做传奇,做传说,但是拿历史来进行戏剧化和讨论并不容易。现在也不是一个历史剧的低潮期,而是历史剧发生了分野。
所谓“分野”就是我们的历史剧逐渐呈现由官方修史的视角向私人历史的视角转化。从《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到《天下长河》,它们在整体的历史观上是非常不同的。过去我们总是以正史的观点为唯一的史观,但是今天我们不再满足于古代史官的记录,而开始用更新颖的方式来观察历史和表达历史;我们现在写历史剧,更关注的是历史中个人的命运、个人视角的表达和现代人的观点和视角。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它表达了个体的迫切的声音。
所谓历史剧,按黑格尔的说法,其实就是当代人通过历史看自己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已经说得再精妙不过了。当代人通过历史看自己,这是历史剧唯一的在戏剧上的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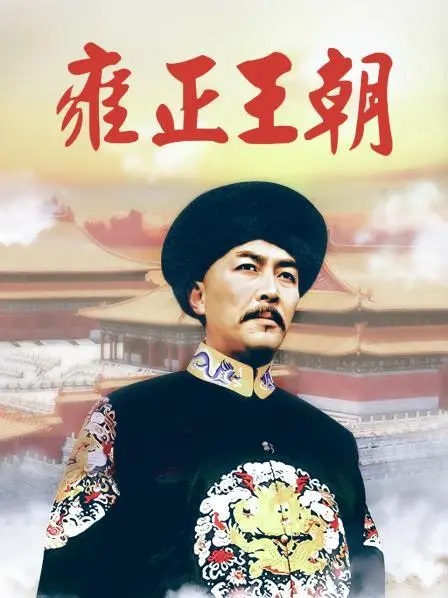
文汇报:从创作层面来说,用更新颖的方式来观察历史和表达历史,意味着很多新的挑战和空间。就这些年的实践而言,有哪些值得分享的方法论?
张挺:《大明风华》和《天下长河》这两部戏都是我写的剧本。《大明风华》更强调人物在历史上的电光火石一样的东西,因为它跨度长,人物多,集数也够,它足够伸得开手脚,因此它讲述的是一个庞大世界中的众生相。
相对来说,因为《天下长河》要处理历史题材,要求更靠谱、更结实。在《天下长河》中,你会更加认真地要求它要尽可能地在历史上有一些影子在那个地方放着,但《大明风华》不一样,因为实际上大明王朝的史料很多地方都是大段的空白。即使是一些目前的记载,随着新史料的出现也会产生极大的偏差,哪怕你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研究者,看着都触目惊心,觉得不可能会有那么大的偏差,但是它确实出现了。
所以我们面对一些可疑材料的时候,会优先去看重戏剧和人物,所以《大明风华》会产生更多诗性化的表达、戏剧的表达、人生的况味,但是《天下长河》首要的是展示那个时期两个技术官员的人生,它们的写法不一样。
黄志忠:看过《天下长河》的观众朋友,我想都会有这种共鸣:一个人物的精神,是靠一场戏一场戏堆积起来的。每个人对如何跟人物建立关系,心里可能都有不同答案。有些是技术上的一些办法,比如情感浓度很深厚的词,我要说得轻,这实际上是一种技术,但是往往这种柔软特别真实,又特别打动我。所以艺术这东西,有时候很娇气,也很讲理,差一点就不是那个味儿,它可能就浊了。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不断地试分寸火候。在现场有时候就神神叨叨的,自己在那儿琢磨,一遍一遍地琢磨,找分寸,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过程。
至于靳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史料上也都有。这个人物形象,通过影像呈现出来之后,能跟观众之间产生多大的情感互动,我觉得这是一种价值的输出。

《人间正道是沧桑》里的杨立仁是某种意义上的反面角色,可能从创作维度来说,他更加具有丰富性,因为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发动机。在人物的建立和设置上,可能有一些更宽泛的东西能来让你表达。靳辅则是一个正面人物,我自己的体会是因为人类的幸福都是相通的,但是痛苦是不一样的,面临痛苦、面临绝境,才能激发出这个人的创造力,所以我在捕捉正面人物的时候,努力找他的死穴。不管是职场上,还是情感上,我有意识抓他的“七寸”,把这些东西放大。在我看来,这是这个人物独特的地方,跟其他人物有区别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一部戏中的所有人物想成一幅油画,那么你在这里要负责什么色彩,你就要填充它。同时还有很多作为配色的颜色,它就像一棵树一样,从出场到最后结束,那么多枝杈要怎么来丰富,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每一场戏都不容小视。戏剧营造的就是一个场,一个人物关系场。演员在镜头前也是一样,演员和对手之间会形成一个场,这个假定性的场就形成了一种戏剧关系,怎样才能在众生相中让别人记住,让这个角色有光芒,我觉得关键在于创作主体要对人物有破坏性,这个破坏性是隐藏在字里行间背后的认知。有时候剧作本身要呈现的是一种情感高度,但是在对手之间我们演着演着它就不是那个劲儿,不知道往哪去。这时候我们会跟导演交流、跟对手交流,说这场戏有可能会到哪儿。我们最后的目的就是进行情感上的输送,让每一个观众被这个人物感动。因为情感是一种共通的东西,能让观众建立同理心,或者用现在常说的说法叫共情力。
实际上,演员只是创作的一个环节,整个创作过程其实是一个组队形的过程,从源头的文本到导演到主创的审美是否一致,到整个拍摄几个月下来,你的精神高度是不是一直吊在一根线上,都是影响的因素。一部戏拍出来,比如说《天下长河》,我们要拍四五个月,不是说进组拍一天就结束了,你不断地要在场中吸收养分,不断地要调整自己,不断地翻看史实,找一些能够对人物有帮助的素材,这个过程很幸福,但是确实也很拧巴和纠结,需要一个很好的身体来支撑。
采访:苏恩祺、赵偲源、王都
编辑:范昕
策划:邵岭
责任编辑:邵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