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集中的作品大多写于2020年7月至2022年4月之间,前后跨度近两年。中间尽管也写了其他的小说,但并未收录其中,我希望它们是一个主题、不同位置间的探讨,质量均衡,各篇目间彼此相连又彼此独立,我希望自己完成了此一预期,当然,仅是希望而已,评定权不在我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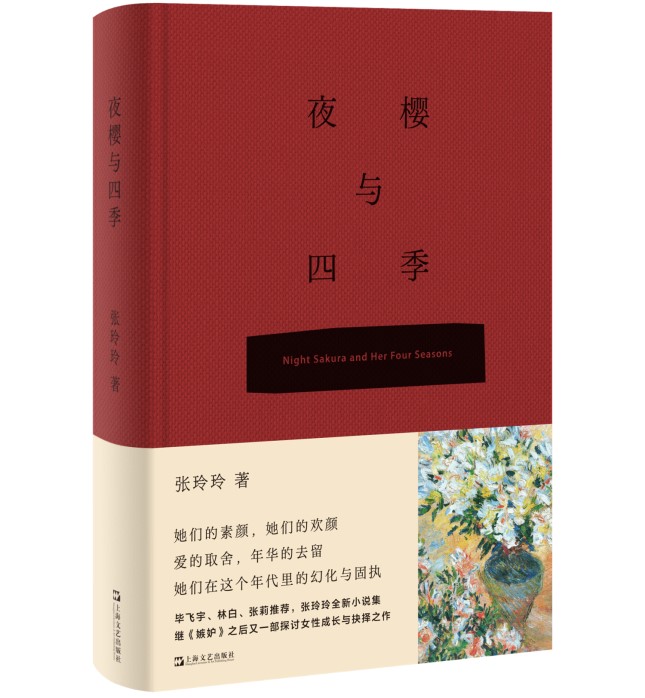
《夜樱与四季》
张玲玲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移民》是最早完成的一篇,也是我七年记者生涯的一次总结,此前尽管做的基本都是财经报道,但我从未将商人群体纳入小说写作之中。一方面觉得情感、经历皆相去甚远,二是在处理此类人物或题材上尚未找到一个能够自我说服的办法。现在的方案未必是最好、最合适的,但却是一种办法。写完没多久,我自觉生活与写作都难以为继,于是辞职,离开上海,去了广西,在那待了一年。
我不可避免地怀抱着重建生活、搜集素材的期望,所以在那的一年间,我尽量写下了自己的生活与观察,作为训练或是储备。其中一些故事与细节,略作修改后进入到《江洲月》内,其主体故事也正是来自于美容院的一段讲述。当我站在今天,重新回看那些笔记和速写,我觉得它呈现出一种故作的轻松,那种愉悦和我当时的整体感受其实大相径庭。我确实去了一些地方,遇到了一些人,但绝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坐在租来的民宿的厨房内,对着屏幕写作,我的右边是隔断墙,左边是钢制水槽、小冰箱以及花15块钱从超市买来的电暖炉。那炉子不能开很久,每隔一会儿时间我就得起身,把它关掉,以免它因温度过高而起火。傍晚时分,我坐在阳台,看着西山、河流,以及地面缓缓上升的灯火。那里有着数不清的雷暴与大雾,就像诸神在持久地发怒。人们贫穷而多病,不得不一再求医问卜。公寓楼下是个临时菜市场,每天我都会下楼,找附近的农民买点蔬菜,许多食物我闻所未闻。我见过一个骑摩托车男人深情地和后座笼中的鸡对视,仿佛那是他的爱侣,而他不得不把它卖掉;我也曾遇到建筑工人们在积满水洼的废墟里放炮竹,他们看到我,快乐叫道:“阿妹!来玩!来!”我想起卡森·麦卡勒斯的童年故事——她感到花园的围墙之内有个派对,那里面人人兴高采烈,但她却从未获准参与;或是西蒙娜·薇依的感触——她没有受邀进入那个房间。她被隔离在外。我对生活的感受也一样,我们都隔着玻璃看,却无法参与其中,这些陌生的邀请总是让我很感动。
邀请,但仍隔着玻璃。我不知道自己花了多久时间才有勇气承认那不是自己的地方,根本无法留下。那些笔记的乐观语调,本质上正是对这种窘境与错误的遮掩,所以每个趣味事件乃至人物速写的背后(龙舟赛、龙舟宴、去丹洲等等),它都有个看似突兀的急转直下的结尾。尽管我们可以说,人生没有对错,而写作的意义之一,即是将所有挫折转化为礼物,至少看起来像个礼物,但仍是一段歧路。我也可以看到那段经历的益处,譬如,我真正开始了一个全职作者的生涯,度过了一段焦灼但也平静的时间。它允许我停下思考,而我已疾行太久;它也向我指出,那种记者似的写作方式应该告一段落,故事不该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寻。

2021年春节,我开始写、改此前写的小说,《面具》即修改于此时,原稿17000字,在《大益》主编陈鹏的建议下,删去了4000字。同一时期,我开始写作《四季歌》。最开始这是一个讲述俩兄弟的故事,但写的时候,梁波与杨绥之间的关系更突出,我便将重心放在他们之上,第三人的加入使得故事走向再度发生了改变。我不想写都市情感故事,尽管它们看起来是也很难被认定为其他,但我仍然觉得那非我的旨趣所在。小说的动因始终是“爱”而非“爱情”,它延续的是《似是故人来》对于个人幸福、历史记忆的探查和思考。后来的很长时间,我都在修改它,不是内核而是速度。我带着稿子在不同城市间穿梭,感受着每个城市不同的流速,这些流速也影响了我对小说的阅读观感,许多时刻的修改正是基于此而来,它是一个叠加了内心自我和历经城市的平均速度。
在写一个未收录的中篇小说时,我彻底离开了广西,回到了杭州。离开的原因和离开上海的原因大致接近。《奥德赛之妻》写于同年11月,取材自大学时期参与戏剧社和后来参与戏剧工作的经历,因为资料足够,成稿也较为顺利。但我真正想写的还一直没写出来,也就是《洄游》,讲的是渔嫂及一起船难。所以除了基本的资料搜集,我又去了几次奉化桐照,看看自己还能发现什么、有何遗漏。
在回忆自己的写作时,我总想起亚里士多德谈诗作——最重要的是专注,决定一个目标,然后贯彻下去,心无旁骛。事实上,就我的实际写作来看,最初的写作意图极少能被贯彻下去,我的计划一直在被各种各样的新事实、新感触所修改,不断演变的事件进程、不断增补的素材资料、实际写作中的种种阻碍都可能让整个计划彻底转向,除非故事够短而我写得够快。或者这样说才对,我的早期想法太天真、太愚蠢,所以根本不堪一击。最终的成稿舍弃了许多东西,但可能比此前略微清晰。小说写作某种意义上就像是对真实人生的模拟,一个句子就是一次抉择,我们面对的都是大片的空白,不安的忧惧的未来,所以迟疑着踌躇着不知将步伐踏向哪里。

我很难说清为什么小说对我有着持续不绝的吸引,我对小说的兴趣和期望远大于我对自己人生的兴趣和期望,我反复审视她仅仅因为她是一个最直接、最长期的观察对象。我在这里谈了太多写作之事,而实际上我应该写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作者跑来跑去,寻找自己的根系和主题、一个人跑来跑去,寻找自己的定居之地,但我没能完成,写不出因为这不完全真实,真实就是她和她都失败了,就像今天的讲述一样,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失败是如何产生而目的是如何偏移的,她们可能获得了某些答案但同时她们也清楚那些答案都是阶段性的,这几年她们感到的否定数目远超她们苦苦想获得的肯定。但奇怪的是她们仍然如此乐观,因为于其而言,小说就是乐观,它根本不是悲伤的沉溺的逃避的消遣而是强力的积极的热忱的行动,尽管你看见那个人不过坐在那边日复一日,所有的冲突与争斗都发生在内部,但通过这样的尝试,它将反复捶打你的精神,再以某种意外的方式作用于你的现实。我努力工作不仅因为我始终坚信,还因为我拒绝相信——不信真理已被揭示,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古典时期即包含着全部的真理,我不信生命是一次次徒劳凄凉的往复,而人类就是一步步地走向衰微、行至末路。希望,厄尔皮斯,赫西俄德写,潘多拉没有听从普拉米修斯的劝告,打开了宙斯赠送的礼盒,所有的礼物都飞了出来,给人间酿成了数不清的灾祸,唯独希望被截住,留在了瓶腹里。所以希望不是礼物,而是包装成礼物的厄运,没有希望的人们反而躲避了宙斯的残酷意志。还是保存这样复杂的缺陷吧,一如情感也是我们的缺陷,我们固执地葆有它们,因为人类的事实就是不完美,因为我们的力量就在其中。
小说集交稿后,我回到了江苏,为下一个作品做准备。这里和杭州、广西都不一样,它有着无止无尽、自由丰沛的晴天,而我其实已经忘记了生命的前17年正是在这样的晴天里度过的。傍晚时分,光线照进西面窗户,房间如同被矿液浸染,黄金在奔涌。我一如既往,最喜欢两个时刻,一是黎明,二是傍晚,它们宛如一次盛大庄严的交接仪式,说着这里的生活凝滞不前中仍有其缓缓的流动。午后时分,如果写得顺利,我就会下楼,去护城河那边走走。然后驻足,在河边长椅上坐会儿,风吹过树梢,空中一丝云也没。那些时刻里,我会想起读过的诗歌,它们和鸟鸣交融在一起,是我听过的最动人的曲调,但我很少会想起那些已写过的小说,词句和故事都渐渐陌生,离我远去。此刻更是,它是个实体、一个出版物,已被讲述的,不能再重复,我无法为之辩解。如果还能说什么,我想那是一个人或一些人过去的几年,她们的时序,他们的季节,她曾在他人的故事里获得过宽慰,也感受过战栗,所以她携带在身,以至成了她的一部分,而今她拿了出来,交还给他们自身——冀求着,我们能短暂地免于孤独。
(本文摘选自《夜樱与四季》一书后记)
作者:张玲玲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