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展人萨雷与米罗《蓝天上的人与鸟之舞;火花》。
胡安·米罗星空中盘旋的飞鸟,傅山潇洒自如的草书七绝诗屏,安德烈·马松如梦如幻的光电树影,龚贤苍劲古厚的树木山石……法国蓬皮杜中心“镇馆之宝”与上海博物馆“文物瑰宝”,奇妙地相会在西岸美术馆将于明天揭幕的年度特展“本源之画——超现实主义与东方”。这是国际策展领域不多见的跨越古今中外文明的对话,邀请人们聆听中国传统绘画中讲究的“书画同源”,如何在西方超现实主义绘画中产生韵味悠长的回响。
近期,申城的海外引进大展此起彼伏、精彩纷呈,然而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引进,也一直是人们思考的问题。在业内看来,由西岸美术馆、上海博物馆与法国蓬皮杜中心携手推出的这个展览,给出了一种有益的探索——在国际视野中平等对话,为跨文化、跨国界、跨馆际的交流与合作开启全新视界。同时,这样的比较视野也有利于树立文化自信,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颇具启示意义。
循着东方视角,打开观看超现实主义的另一种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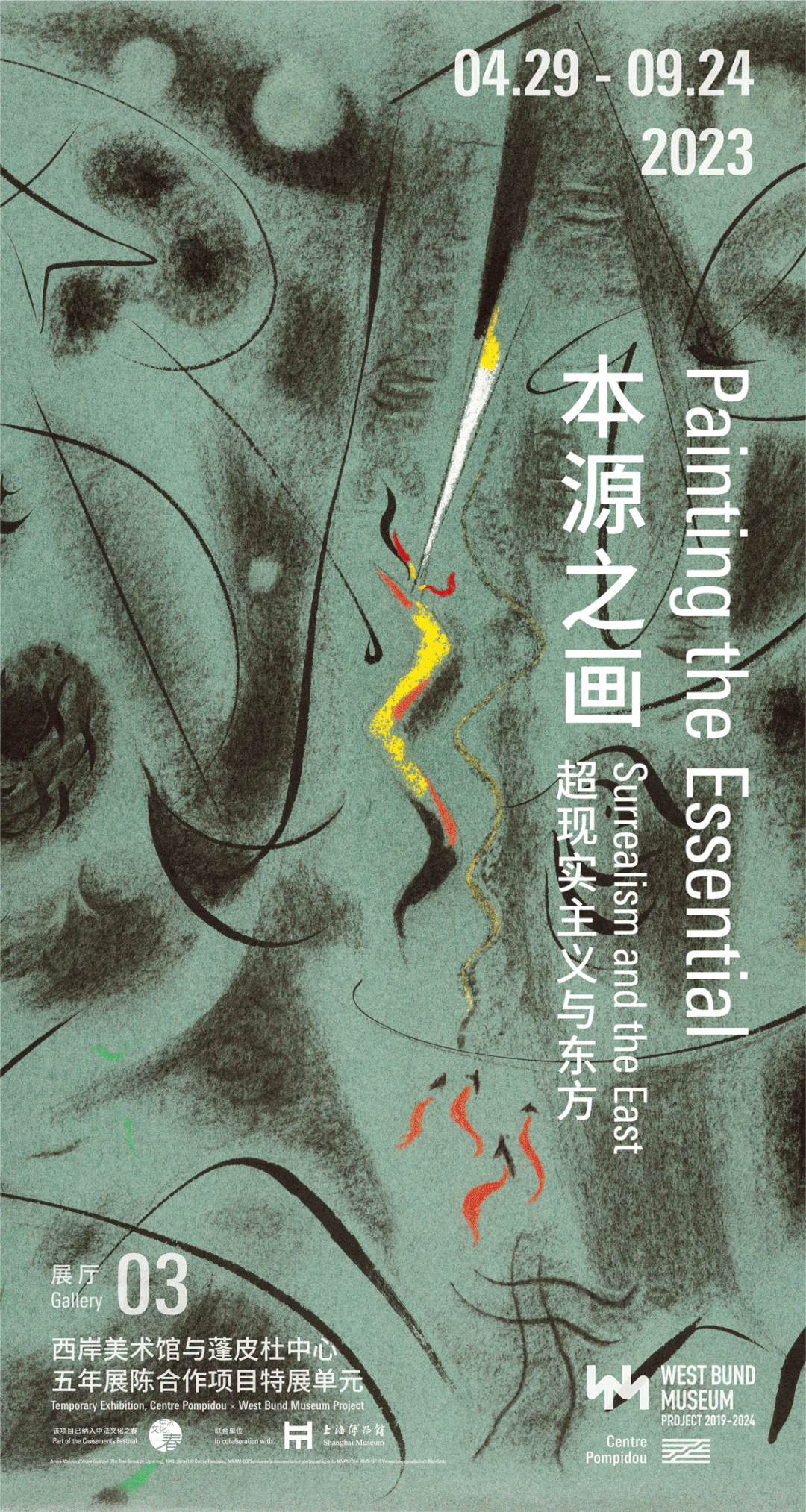
记者昨天在预展中看到,作为蓬皮杜中心“镇馆之宝”之一的胡安·米罗《星座》系列22幅画,被布置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展厅内。置身其中,能够感觉到画面异想天开又深邃宁静的氛围。接受本报专访的展览联合策展人、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现代收藏部策展人玛丽·萨雷说,西方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表现出的对于宇宙以及大自然的关注,也是中国古代画家一直重视的。
超现实主义,通常被认为以1924年法国诗人安德烈·布勒东在巴黎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为起点,更像是一场精神性的革新,涉及文学、绘画、音乐等诸多领域。此次展览为何选择聚焦超现实主义?在萨雷看来,这是因为在西方艺术史上,鲜有绘画艺术运动像超现实主义一样,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建立起真正的美学对话。
“绘画的现代性,让艺术家对他者文化开始产生兴趣。例如野兽派、立体主义,都是从非洲艺术中汲取了营养。而像超现实主义,它的很大一部分灵感则来自东方。”萨雷坦言,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超现实主义诗人和画家们试图在失望的情绪中寻找救赎。他们在东方文化中发现了一个绘画与诗歌密不可分的世界。东方的文明,特别是中国古代文人画家所倡导的“书画同源”,深刻影响了不在少数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
萨雷向记者透露,超现实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联,此前从未被充分讨论过。这种关联不仅让中国观众感到陌生,就连西方观众知道的也不多。因而,这次展览其实带有一些研究的意味,以十个章节的近百件作品启引人们发现一大批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都曾“偷师”东方。例如,此次展出的安德烈·马松的多幅作品,一方面呈现他受中国绘画与神秘主义影响从而将绘画与书法融合的实践,另一方面折射中国宋代绘画特别是风景画中景深对其作品的启发。而在让·德戈特克斯的一系列抽象画中,可见对于东方禅学思想的吸收。
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诗人、画家亨利·米肖与中国画家赵无极的“碰撞”,在展览中构成值得玩味的片段。此二人1950年相遇于巴黎,此后结下深厚友谊。彼时,从中国来到法国巴黎学习绘画的赵无极,竭力想要在创作中摆脱其书法训练的影响,从零开始吸收欧洲的绘画,可最终让他在艺术史上留名的抽象画,处处体现着中国绘画的核心特征,如自然景观的呈现、构图中的留白、透视的消失、符号的涌现。而米肖则为东方艺术深深着迷,用墨创出的黑色符号,被赵无极比作“表意文字”。
在萨雷看来,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的五年展陈合作,给跨文化对话带来绝佳的契机。她希望未来这样的展览能再多一些,也很期待来自西岸美术馆的策展人明年将中国绘画的展览带到蓬皮杜中心。
与超现实主义有类似理念的中国传统绘画,值得更多了解

董其昌《燕吴八景图》册之一。
对照蓬皮杜带到西岸美术馆的展品清单,上海博物馆从成千上万件书画藏品中精选出了包括梁楷(传)《布袋和尚图》卷、董其昌《燕吴八景图》册、八大山人《果熟来禽图》页、恽寿平《山水花卉图》册等16件作品。这些中国古代书画珍品此次与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杰作同置一室,将于全展期内分四批呈现,其中第一批有七件。“从形式到理念,我们选的都是相似度比较高、能够形成对话的作品,少而精。”负责此次从上博馆藏中选件的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告诉记者。
凌利中举例道,朱迪特·赖格尔创作于1958年的油画《主宰的中心》与明末清初八大山人的水墨《果熟来禽图》页,即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对应关系。赖格尔的画,乍一看有点像东方的太极图,俨然抽象的笔墨在旋转。八大山人的画,画的是一只小鸟栖息于一块石头上,整体呈现出颇有混沌感的圆形观感。“这两幅图无论外观还是构图,看上去都很类似。值得一提的是,赖格尔运用的这种近乎黑白的艺术语言,也接近中国的水墨,尤其带有一种和中国书法类似的书写性,从中能看到动感以及疏密轻重变化。”
超现实主义,最早由诗人创立,意欲超越时间和空间。凌利中指出,诗化与书写性,是其中的两个关键词,均带有一种主观表现意味。而这两个关键词,也恰恰是中国传统绘画一直以来推崇的。先看国画的诗化特征。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一直在用一种诗人的思考方式来进行绘画,构成一条写意化的轨迹。唐代的王维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鼻祖,他是诗人,也是画家,留下过画“雪中芭蕉”的典故。大雪中怎么会有芭蕉?这就是一种超现实主义。北宋的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三远法”,用几种不同的透视角度表现景物的“高远”“深远”“平远”,在同一幅画面中集齐“三远法”。这不也恰恰是超越时空的诗意吗?再看国画的书写性。在中国,书法和绘画千百年来源远流长,交相辉映、水乳交融。元代赵孟頫明确提出以书入画,有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超现实主义的很多理念,在我们中国传统绘画史中,都能找到源头。”凌利中坦言,国画很早便体现这种理念上的革新了。无论南朝齐梁时期谢赫在“六法”中提出“气韵生动”“经营位置”,还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提出画人物“迁想妙得”,都是一种与超现实主义类似的理念,宋元以后,更将这种理念付诸实践。“人们会恍然发觉,很多时候西方现代艺术史似乎是跟在中国传统绘画之后一步步走过来的。只可惜这样一种领先,绝大多数中国观众并不知晓。”
凌利中说,中国传统绘画介于似与不似之间,有宋画的写实,但又不像西方绘画写实到让人产生错觉,也没有走到纯抽象,出现康定斯基这样的艺术家。“这恰恰显示了一种东方哲学与智慧,里面有一种分寸感,值得学界研究,也值得中国观众加深了解、细细领悟。”
作者:范昕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邢晓芳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