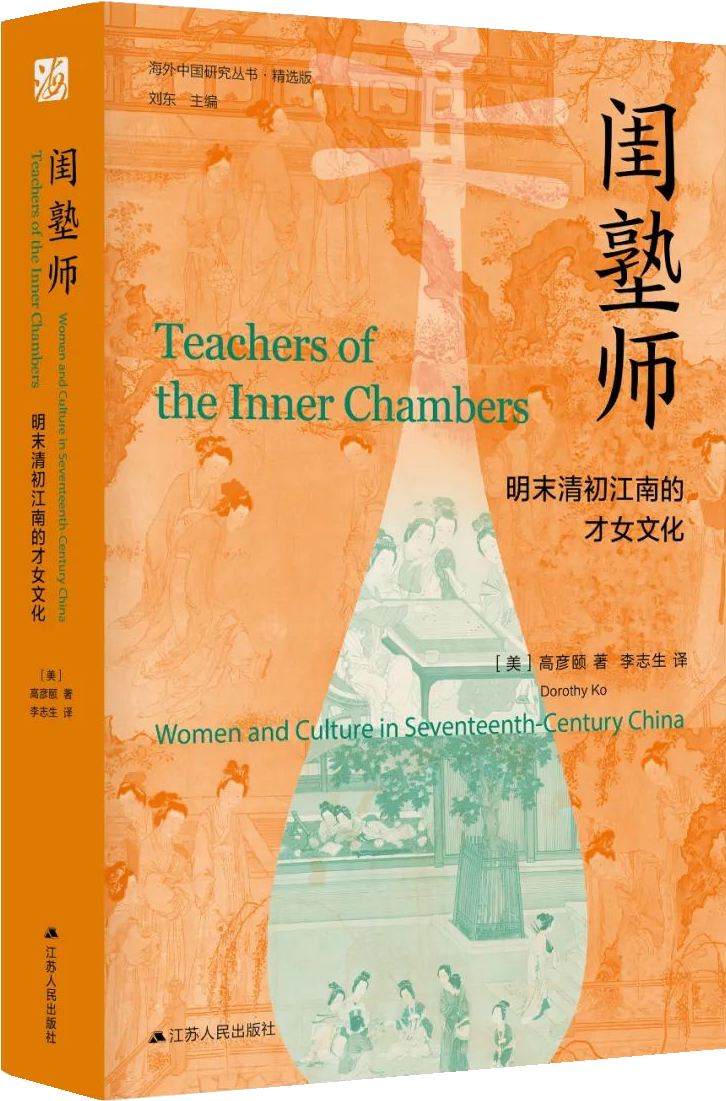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美] 高彦颐 著
李志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明末清初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促进了“才女文化”的繁荣。其中最突出的是坊刻的兴起、读者大众群的出现、对情感的重新关注、女性教育的提倡、女性出游机会的增多及女子特性的重新定义等。
本书作者指出,明末清初的江南闺秀远不是受压和无声的,她们在男性支配的儒家体系中创造了一种丰富多彩和颇具意义的文化生存方式。作者通过儒家理想化理论、生活实践和女性视角的交叉互动,重构了这些妇女的社交、情感和智力世界。透过妇女生活,本书提出了一种考察历史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是以具体了解妇女是如何生活为前提的。
>>内文选读
女文人:如有威望的男人一样的职业作家
第二类“职业女性”——职业作家的流动性,也很难与儒家社会性别理念的内涵相吻合。王端淑不平凡的生涯,证明了女性职业作家面对的是怎样的更为复杂的通融情况,这种通融介于家内和公众领域之间,同时也介于男性和女性领地之间。
有着八位兄弟的王端淑,生于绍兴府山阴县一个博学家庭。其父亲王思任(1575—1646,1595年进士)是一位著名的小品随笔作家,他以其深刻的幽默而著称。当1646年清朝军队横行于绍兴时,王思任因年纪过大而未能参加海上的忠明抵抗,但他在门上贴出了“绝不投降”的标语,拒绝接受清朝的剃发令,并退至山中绝食而死。王思任的气节及其忠明的信念,对其女产生了长久影响。
王端淑作为作家的职业生涯和造诣,与黄媛介十分相像。王端淑之父的仕途为经常的赋闲在家所打断,王端淑受教于父亲,她对历史和儒家经典非常精通。如黄媛介一样,端淑是一种艰深的汉代文体——汉赋的专家,也是一位有造诣的画家。王端淑是一位塾师,也被邀赴京教授宫中的女性,但这一邀请被她拒绝。两位女性都为李渔的剧作写过序,李渔是她们共同的朋友。两人都受过良好教育,都比她们的丈夫有名望和被更多地雇佣。综合这些,她们构成了明末清初女文人的典型范例,这些文人女性凭着自己的文学和艺术天才谋生。
两位女性所走的路非常相近,所以她们很有可能于清代早期旅居杭州时见过面。通过兴盛于西湖周围的诗社和其他文人组织,她们明显有着许多共同的朋友,包括李渔,西湖是当时艺术赞助网的中心。尽管没有文字材料证明她们之间存在着深厚友谊,但两位有才华的女性偶尔会对相互的作品进行评论。在一篇精心解释黄媛介诗句的诗作中,王端淑赞扬了其艺术技巧:“竹花吹墨影,片锦贮雄文,抹月含山谷,披云写右军。击音秋水寂,空响远烟闻,脂骨应人外,幽香纸上分。”通过将媛介与著名书法家王羲之(321—379)130和宋代优秀词人黄庭坚(1045—1105)相比较,王端淑明显是有目的的。如我们将看到的,上层寡妇商景兰首先将黄媛介置于一个女性谱系中,与此相反,王端淑则视她的朋友,可能也是她自己为男性书法和诗歌天才的传人。

王端淑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较之家内女性,女作家的生活方式和关注点与那些公共领域中的男性更接近。王端淑是一位极为多产的作家和诗人,在清朝征服后不久,她便以职业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围绕着其决定的争执显示,在她的家人眼中,女性职业艺术家的地位是成问题的。毛奇龄(1623—1716),一位来自其同乡绍兴府的学者,就她的动机生动地写道:“今玉映以冻饥轻去其乡,随其外人丁君者牵车出门。将栖迟道路,而自衔其书画笔札以为活。”毛奇龄说得非常清楚,王端淑现身于社交界是迫于其家庭的穷困。但他们绝不是其时唯一受到改朝换代劫掠的上层家庭,这一事实反映,这些家庭中的男性没有供养家庭成员的能力。
尽管不晓得丁圣肇族人的反应,但端淑的兄弟们则都因其现身于社交界而略感窘迫。端淑出发前,她的哥哥们曾试图劝阻她。她将这些争论写在一首长诗中。她哥哥反对的理由是:“长兄诘小妹,匆匆何负笈。昆弟无所求,但问诸友执,且父海内外,如何人檐立。兄等制衣裳,各弟出供给,舍此去倚谁,睹悲气亦唈。”端淑回敬道:“阿翁作文苑,遗子惟图籍,汝妹病且慵,无能理刀尺,上衣不敝身,朝食不及夕。”她申辩说,她只能“舌耕暂生为,聊握班生笔”,意即她只能以教书和写作为生。
王端淑继续为其于公众领域曝光的合理性进行辩解:“诸兄阿弟幸无虑,当年崇嘏名最著。”黄崇嘏是一位颇具才情的女性,她曾假扮男子一年,并使自己成了前蜀的一位官员,她是女性僭入公众领域的一位令人尊敬的先驱。一旦当公众领域中的女性意识到穿或不穿男性的外衣,她的家内领域和他的公众领域间的严格的意识形态界限都在事实上是可以超越的时候,她们就可以起到替代男性的作用了。将穿着男女兼有外衣的黄崇嘏视作自己的偶像,王端淑看起来正是要将自己扮演成那样的角色。
王端淑的反驳令她的兄长哑口无言。“兄弟闻予一篇言,面赤各各相偷觑,兄辞有事暂先回,弟辈尚欲往他处。”端淑继续道:“万分无奈择初三,携书哭别含悲去。”最后,她还不忘取笑她的兄弟:“慎哉始信毛诗云,兄弟之言不可据。”不管他们当初是怎样的反对,端淑的兄长们后来还是对她的出版历险给予了支持并为她写了贺词式的序言。王端淑的成功不但没有给她的家庭抹黑,反而为王家的声望添了光。尽管其父思任早在端淑公众职业生涯开始之前就已死去,但在一篇评论中他就预言,只有她有着他继承人的才华:“身有八子,不及一女。”他带着自豪,非常清楚地视她为儿子的替代者。
女作家如黄媛介和王端淑,被她们的男性亲属意识到了是在从事男人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感觉是客观正确的。在王端淑的例子中,她仅是出于生计,而追随父亲出售作品和书画。尽管所有文人偶尔都会应那些能够付得起钱的男、女的请求,而撰写墓志铭或传记,但王思任是以此酬金为固定收入的。思任被说成是“钱癖”。依他的一位朋友所说:“遂东有钱癖,见钱即喜形于色,是日为文特佳。然其所入者,强半皆谀墓金,又好施而不吝,或散给姻族,或宴会朋友,可顷刻立尽,与晋人持筹烛下溺于阿堵者不同,故世无鄙之者。”除了教育,端淑很可能也受益于其父的社会关系。由王思任开始,为钱而写成了这个家庭的传统;尽管端淑是女儿,但只有她才是他最有才华的继承人。

不仅代替了儿子,而且在文人圈中,端淑也成了丈夫的替代者,尽管她的丈夫丁圣肇经常伴其左右。如,端淑为其丈夫代笔向南明朝廷上奏文,试图为他的父亲——一位死去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实际上,王端淑以其丈夫的名义,撰写了大量的诗歌、书信、挽歌、传记和墓志铭,以至于有些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以为他没文化。她甚至替他坐在其诗社举办的赛诗会上。非常明显,王端淑喜欢这样的一种角色颠倒,她采用男性的声音写诗,其中一首幽默地题为《效闺秀诗博哂》,使自己置身于女诗人的典型风花雪月题材之外:“烟炉宿火熏鸳褥,堕燕新泥污绣鞋,步出素屏聊遣闷,凄凉又听鸟喈之。”
王端淑不仅擅长男性喜爱的风格和心安理得地装出男性的声音,她还在传统上被视作男性的题材上胜出。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1648年和1649年她所写的一系列传记上,这些传记是为殉难的忠明之人所写的。对男性来说,颂扬投井、跳河或咒骂兵士以防被奸的女性是很常见的;端淑循着男性的惯常作法,颂扬了九位这样的忠诚殉国者。殉国者中的四位明确说是会稽人;因此王端淑可能是从口头文字得知他们行动的。但更不寻常的是,她写了为垮台的王朝而死的六位男性的报道。
端淑描述了当时的心态:“自管文忠至金陵乞丐六传,皆予戊巳间之率笔也。时以丧乱之后,家计萧然,暂寓梅山,无心女红,聊借笔墨,以舒郁郁,愧未成文,恐不免班门弄斧之诮。”尽管她不能明说,但她的“挫折”更多地来自于她只能欲言又止的对明室的忠诚,而不是其个人的经济困境。在端淑对忠明英雄的描绘中,她有意区别于男性所写的正式祭文,男性祭文着重于这些殉难者的家庭血统或公众职业生涯,而她则着眼于导致他们作出决断的事件和内心斗争。她对关键时刻的个人信念非常感兴趣,她并没有将忠诚视作一种抽象的道德。作为一位忠明之士,她同样被两个性别和所有阶层成员所表现出的气节感动。

……
乍看起来,职业女性作家和艺术家似乎在威胁着其时流行的社会性别安排。有什么能比女性养家更是对“三从”的有力颠覆呢?然而,就像这样的社会性别倒置现象可能给女性的夫、兄带来的窘迫一样,它并没有破坏社会性别体系的前提。在赞扬王端淑作为女性是如此的不平凡,以至于应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男性时,她的男性支持者在不言而喻地坚持着将男性归于更高价值层面的社会性别等级,他们视男性有很高的文化成就、关心公众事务、英雄化情感的文学展现等。尽管单个女性因此获得了解放,而在通常情况下,这种解放是其同性成员在没有危害其良家身份的前提下不会获得的,但社会性别体系的总体不平衡依然存在,甚至更加强化。
>>作者简介
高彦颐(Dorothy Ko),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历史系博士,现为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Barnard)学院历史系教授。代表作有《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和《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等。
作者:高彦颐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