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迈向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中,人的幸福与福祉渐趋成为社会的基本安排,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如18世纪德意志思想家洪堡所说:“古代的国家关心人作为人本身的力量和教育,近代的国家关心人的福利、他的财产及其从事职业工作的能力。古代的国家追求美德,近代的国家追求幸福快乐。”如何让人们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学术问题。
首先实现个人的福祉或者“个人的私利”
诚如美国思想史家麦马翁在《幸福的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出版)中所说,18世纪是幸福话语表达的爆炸性时刻,众多思想家纷纷讨论如何过上幸福快乐和美好的生活。2022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伟大目标:亚当·斯密论美好生活》一书,巧合的是,译林出版社也在2020年出版了《牛津通识读本:幸福》。的确,从这些以幸福为议题的图书的出版可见在当下的中国,思考什么是幸福,如何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又如何保障人们的幸福生活,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这些著作的出版将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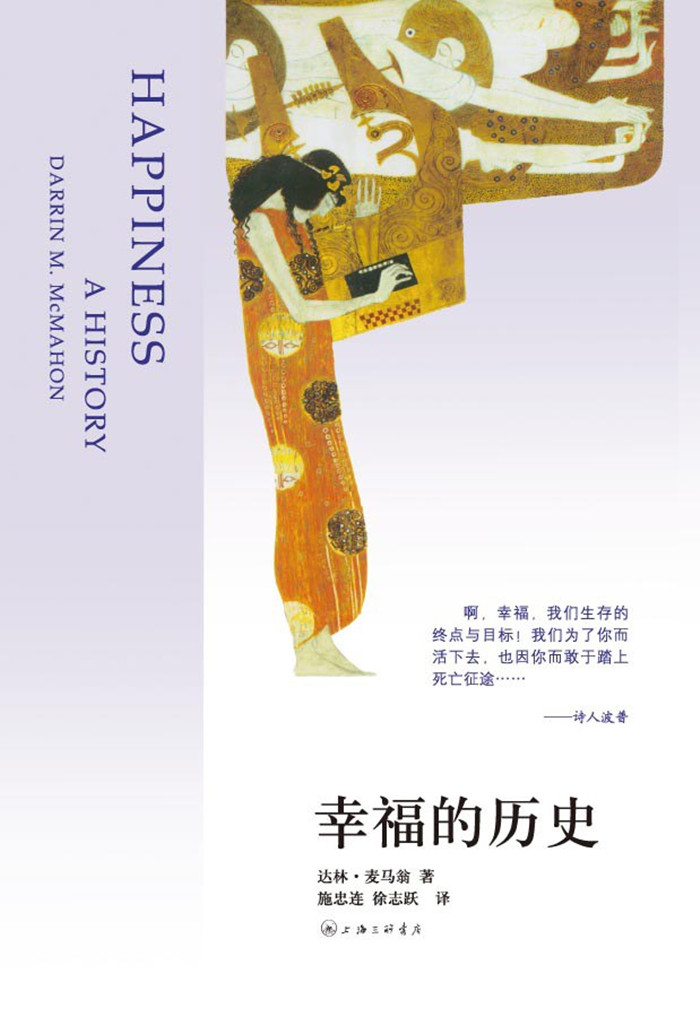
《幸福的历史》
[美]达林·麦马翁 著
施忠连 徐志跃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正如他自己所说,写作这本书的动因就是要探讨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得到了学界很高的评价。历史学家吉本说,这位哲学家向世界呈现了一部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系统的关于贸易和税收的专著,这一专著足以令作者本人自傲,也定会为全人类带来福祉。斯密的这本书虽然讨论的是市场交换和商业社会等问题,但究其实质却是在探究如何实现人类的福祉。不过,在实现人类福祉的路径上,斯密却是从首先实现个人的福祉或者“个人的私利”来完成的。对此,斯密说道:“毫无疑问,每个人天然以自身福祉为首要关切;鉴于个人总是比其他任何人更适合照顾自己的福祉,这一安排是恰当且正当的。”
在《国富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出版)中,斯密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思考过程和令人惊叹的逻辑推论。由于劳动分工的缘由,每个人自我需要的满足也就无法依赖于个人自身的劳动,而是要依靠市场交换。每个人在参与市场交换的时候,其出发点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实现自己的欲望与需求,按照斯密的说法,就是“利己”。想来这也是符合人性本身。早在17世纪时,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就说过,生命的自保是人的本性,同样,洛克将其论证为一种权利,即生命权。在劳动分工日趋细密的社会里,面包师只会烤制面包,那么他维持自己生命所需的其他物品怎么得到呢?或者说,实现自己基于本性的欲望如何得到满足?无疑,只能是通过市场交换。因此,为了自己的必需,为了“利己”,为了让自己过上美好的幸福的生活,他只能兢兢业业把自己的面包做得品质精良,参与市场交换。对此,斯密说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由此,每个人也都成为了商人,按照现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理性的“经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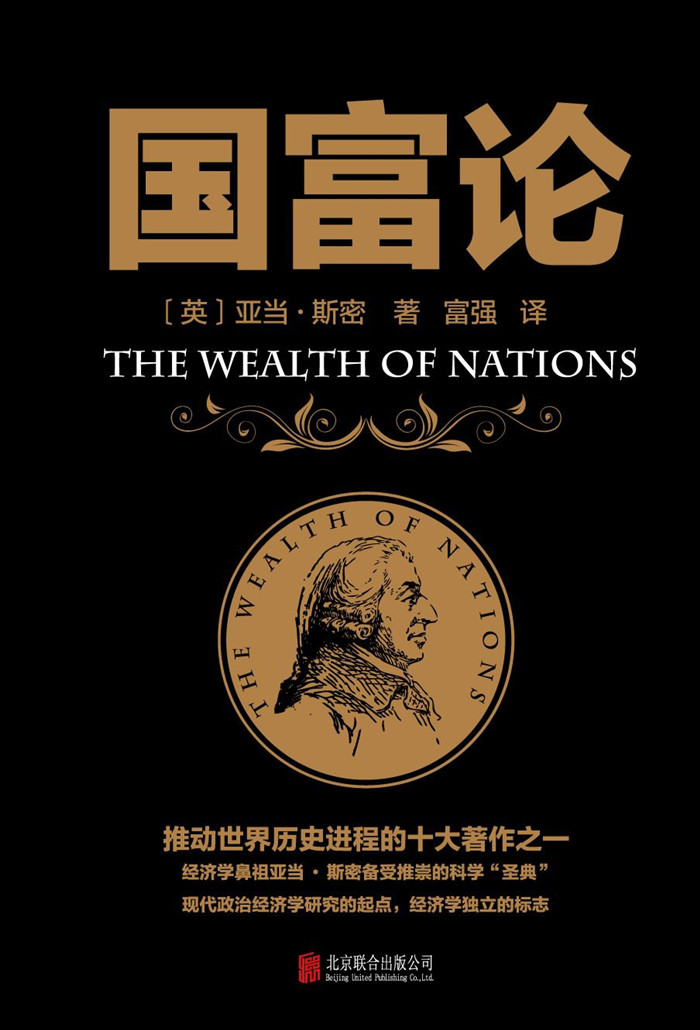
我们必须坦然承认,每个“商人”完全是从利己出发来参与市场交换,并且希望在这个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进而让自己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由此,个体性或个人的利益开始得到凸显,并且成为“商业社会”的动力与基础。斯密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因此,市场的起点和终点均为个人或个体的利益,而非是别人或集体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所说的“自利”不是通常所说的自私自利,在我们的语境中常常把利己理解成为了自私,这完全是一种误读。在斯密那里,正是出于利己的起点,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最后却实现了利他,由此会带来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同时也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完美结合。正如斯密所说:“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口舌去劝阻他们。”
私利怎样转化为社会的公共利益
按照《伟大目标:亚当·斯密论美好生活》一书作者的解读,他认为,自利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它关注的是一种特别具体的利益。这里,自然涉及到对斯密那个时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道德观念,或者说自利与利益在未来新的社会中占有何种地位。17世纪中期之前,“利益”一词的含义较广,例如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就曾说:“人们并不总是把‘利益’这个词理解为一种财产方面的利益,而经常倒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有关光荣或名誉的利益。”虽然如此,但是在17世纪中期开始,“利益”这个词的含义却是日趋收窄,成为与财富相关联的概念。黎塞留的秘书让·德·西隆也说,我不明白为何利益一词总是只跟财产或财富的利益挂钩。拉罗什福科也一再指出:“人们所谓的德行,常常只是某些行为和各种利益的集合,由天赐的运气或自我的精明巧妙地造成。” “德行消失在利益之中,正如河流消失在海洋之中。”尽管“利益”一词开始有了经济上的好处这种更为狭隘的含义,并开始引发出道德上的争论,“利益在后面推动着所有种类的德行和恶性”,“利益——我们谴责它造成我们所有的恶,却常常应该因它促成我们的善行而受到赞扬。”但平心而论,从17世纪开始的近代社会转型以来,个人利益还未得到社会的接受与认可,追求个人的私利仍然被视为是一种恶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714年,曼德维尔才勇敢地写出《蜜蜂的寓言》(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一书,理直气壮地要为个人利益正名。这本书的主题就如其副标题所标示的那样,“私之恶,公之益”(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即积累个人财富的自利行为不仅仅是为了自我,最终却是有利于社会,增加了大众的舒适和幸福。曼德维尔还说:“私利造就了独创性,加之时间和工业,带给了生活以便利,这是真正的享受、舒适与自在,由此,每个穷人也比以前的富人生活得要好。”他举例说,贪婪这个字已被加入了很多的恶名, 但没有贪婪,奢侈很快便会缺少物质基础。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了对人性的理解,在曼德维尔看来,人性中满足自己利益的需要这一欲望是无可指责的。要让人的私利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所有人的私利相遇,并且经过政治家的管理后,私利就会转化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其结果自然就是,“私人的恶行若经过老练政治家的妥善管理就被转化为公众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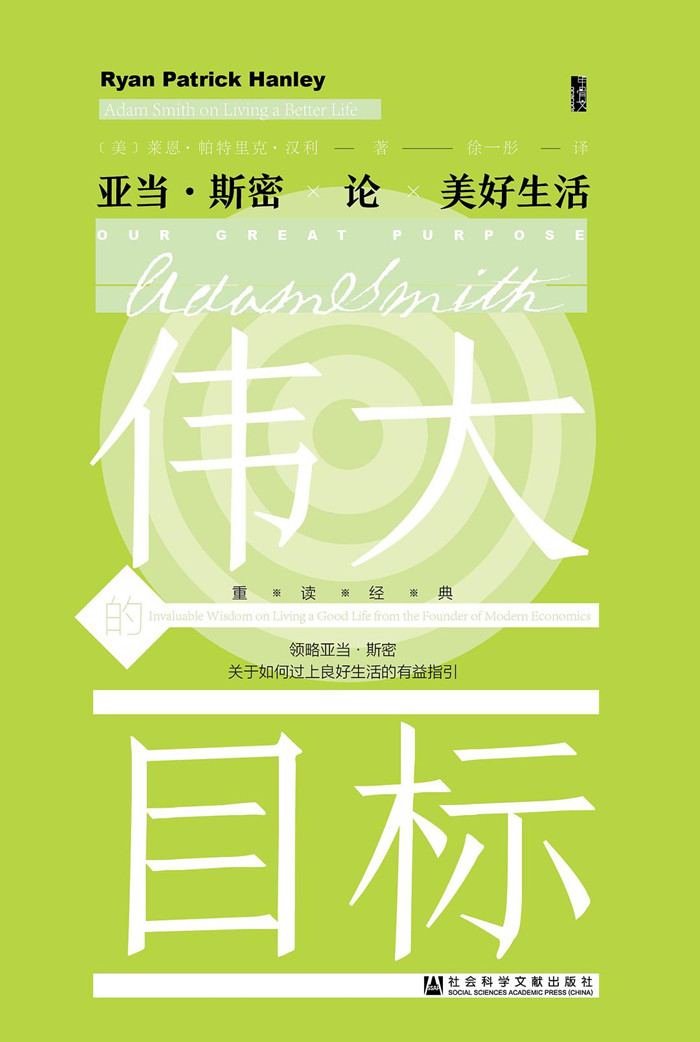
《伟大目标:亚当·斯密论美好生活》
[美]莱恩·帕特里克·汉利 著
徐一彤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亚当·斯密通过他的老师哈钦森以及思想家休谟了解到了曼德维尔的思想,并认真阅读了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这本书,正是在曼德维尔的思想影响下,亚当·斯密系统地将这一思想嵌入到他的“商业社会”这一理论构建中,“无需任何法律干预,人的私利和七情六欲就能诱导他们去剖分和分配每一个社会的库存,这种剖分和分配是在该社会各行各业中进行的,并尽可能按照一种最符合全社会利益的比例而进行”。在他看来,这一道德观将是未来“商业社会”的基础。正因为此,斯密承认曼德维尔的观点是为一种“原创”。

承认每个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
其实,如果将斯密的理论置放到整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来理解的话,更可以明晓斯密的这一理论与整个启蒙运动的思想表述非常一致。研究18世纪启蒙运动的学者罗伊·波特在其《启蒙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这本书中这样写道:法国人爱尔维修与功利主义的开创者、英国人杰里米·边沁等启蒙运动思想家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人性进行了解释,并以此取代传统的道德化人性观,即认为人是一种受到肉欲威胁的理性存在。他们将人视作一种由天性操控,去寻求快乐、躲避痛苦的造物,因此进步的社会政策的真正目标就应该是引导进步的利己之心去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传统的布道者将“快乐原则”视为有罪的、肉欲的享乐主义而加以谴责,但新一派的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著有《国富论》的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则认为,如果个体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自私行为遵循了市场的竞争法则,那么将会有利于公共利益——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天意这只“看不见的手”。无独有偶,以意大利人贝卡利亚为代表的法律改革家也认为,一种真正科学的法学需要建立在理性的自私这一心理学假设的基础上:必须通过精确测算,以确保惩罚导致的痛苦超过犯罪带来的快乐。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设有“幸福”这个条目。另外一位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则断言,18世纪是幸福的世纪。而亚当·斯密也反复宣称,追求个人的幸福与利益,在很多时候是令人尊敬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要尊重每个个体的生命存在,保证其基本的生活要求,承认每个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正因为此,今天重温这些思想家的论述,阅读这些关于“幸福”议题的图书,将会让我们受益无穷,并将激发起我们深深的思考:如何获得幸福?它是被外在地赋予,还是要自我的追求?应该建构起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样式才能免除被外加的痛苦,保证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如何既让自己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也让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实现其幸福?(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牛津通识读本:幸福》
[美] 丹尼尔·M.海布伦 著
肖 舒 译
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作者:李宏图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