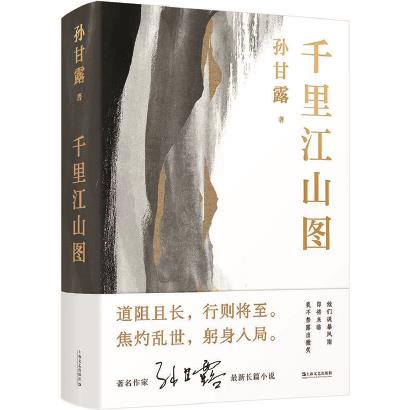
最近孙甘露的新作《千里江山图》出版,无疑值得关注。当年的先锋派主将,“我是少年酒坛子”的豪放绚丽;“信使之函”满纸荒唐言却抑制不住字字珠玑,诗意流淌;而“请女人猜谜”诡异灵动,玄机四伏……。一晃30多年,其中孙甘露也有其他作品,他写得谨慎,小心翼翼,怕是伤着文字,划伤时代的皮肤。甘露干脆把自己献给了文学事业,为上海作协做着日常工作,举办巨型的上海国际国际文学周,偶尔在一些新作的研讨会上发表精辟点到为止的言辞。甘露是令人敬重的作家,日久弥新,他存在,他就永远保持一个作家的状态。虽然归来不再是少年,《千里江山图》却不得不让人惊叹笔法精湛,针脚绵密,机锋内敛。虽然故事危机四伏,分明是十面埋伏的狰狞;他却写得如宋明工笔般的秀丽。20世纪的惨烈,像里尔克的豹子被关进笼子,我们翻动书页,却看到豹子踱着精巧的步子,在那个笼子里,谨慎丈量自己的命运。
书名《千里江山图》用的是北宋年间的名画为题,名画《千里江山图》传为宋徽宗赵佶亲授弟子王希孟在18岁时用了半年时间绘成。《千里江山图》显然表达了徽宗心目中的社稷江山的理想,山青水秀,雄奇气派,太平盛世,天人合一,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当然,孙甘露的立意在当下,这是就是当今时代常说的“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而小说的故事设置是1933年早春发生在上海的故事,我地下党围绕一次秘密任务与敌特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千里江山图》是小说中的接头暗号,小说当然有点题之笔,陈千里到诊所找林石,他以书画商人的身份说“我想找一幅宋画。”林石:“那可不好找。”陈千里:“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林石:“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陈千里:“《千里江山图》。”林石:“你打开窗朝外面看。”陈千里:“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小说的主题由此很清楚,就是一批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为人民打下江山所付出的血的代价,他们不惜牺牲年轻的生命,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人民过上平等自由幸福的生活。这一主题当然是当今的主流主题,或者说红色主题,无数的作品都在处理同一主题,但孙甘露依然能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其笔法正如宋明工笔画,在故事设置、情节结构安排、人物刻画方面,都显示出孙甘露的艺术力道。

小说开场就紧张惊险,我地下党一次布置工作的秘密会议在一个图书馆的密室,不想有内奸向特务机关通报消息,开场就是紧急的疏散和逃离。在这样危急关头,人物一个一个出场,表现也一场比一场危险。地下工作最危险的是出了内奸,那就意味着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生死就是瞬间之事。既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又要防止内奸出卖。猜疑也在革命者内部蔓延,这同样具有杀伤力。谁是内奸?故事突然间展开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完成护送浩瀚同志的任务;另一条是要识别谁是内奸。这两条线索归结到敌特叶启年、游天啸那里,时刻牵动敌特的阴谋与凶险的暗杀。整个故事,悬念十足,紧张惊险,环环相扣,危机四伏。
小说的主题固然是歌颂革命志士英勇无畏,为党的事业视死如归;但小说的写法吸取了谍战小说和影片的特点,完全可以当作精彩绝伦的谍战故事来读。这促使我去思考一个理论问题,“红色写作”——如果可以创立这个概念的话,同样可以有艺术性。此前写红色谍战成功的作品有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风语》系列小说,其中多部改编成电影也非常成功。麦家的《解密》英文版被收进英国“企鹅经典”文库,这也说明写红色主题并非就只能成为意识形态宣传读物,其文学性和艺术价值同样可以得到承认。所以,对于艺术手法高超的作家来说,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当然,如今写地下党的影视作品尤其多,但成功的小说并不多见,麦家的小说并不仅仅属于这个类型,他的小说还具有多元综合的艺术特点,是故其艺术性体现得比较复杂。五六十年代写地下党作品成功的例子有《野火春风斗古城》,要说那时的条条框框比现在要多,但这部作品无疑非常成功,直至今天读来还是同样引人入胜。要说“红色写作”与艺术探索最早结合的作品当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该作品虽然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但莫言却把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恨情仇的故事讲得如歌如诉,再有余占鳌抗日的故事穿行于其中,历史被托起了高度,并被赋予了20世纪的本质。
显然,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无疑要归在典型的“红色写作”的纲要下,这不只是这一群地下党洒热血,抛头颅,最终有一个长长的牺牲人物的名单——革命志士用鲜血染红了江山。小说中着笔不多的老方,却有一个惊人的细节,“那个字很可能是老方用血写的,他自己的血。那是个未写完整的‘山’。”显然,甘露要强调这江山不是赭石朱红画下的山水,而是用鲜血染就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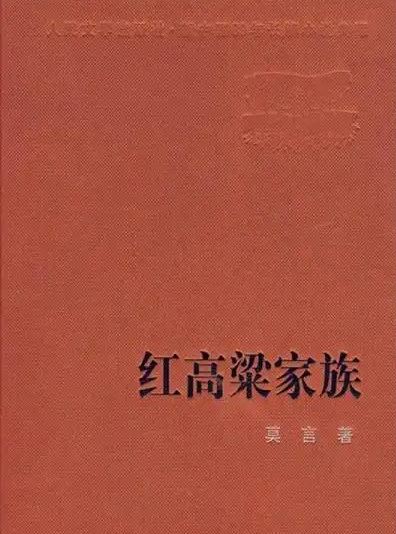
《千里江山图》在艺术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在情节处理上的紧张性与紧凑性。尽管说这是谍战叙事的基本特征,但具体动用却并非易事,做到入情入理,合乎逻辑,令人信服却是要靠叙述功夫。小说以失败开场,以有内奸为悬念展开叙述,一开始就是一个组织成员悉数亮相,人物群体相互关联,故事的展开井然有序,错落有致。陈千里出场,林石被怀疑,陈千里还怀疑崔文泰是内奸,后来凌汶和易君年南下,谁能想易君年就是内奸,就是特务卢忠德假冒。很显然,敌我双方相互潜伏,卢忠德这个“西施”潜伏在我地下党组织中,破坏性极大。但我地下党的潜伏更是厉害,特务头目叶启年的女儿叶桃就是地下党,多少有价值的情报从她这里送出,但她英勇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另一个人物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穆川始终写得隐晦,莫测高深,读者十有八九可以推测,他可能是一个级别相当高的潜伏人员。因为这些线索的交叉,使得险象环生,危机四伏,故事的每一个推进环节都加强了紧凑性,生发出紧张性。
这篇小说值得肯定的是写人物,毕竟是老道的作家,对每个人物都握得紧,刻画得准确精细。正面的人物如陈千里,林石、凌汶、梁士超……,每个人的经历、职业、性格不同,人物形象表现出来的特点也就各异,这才有丰富多样的地下党的群体形象。红色面孔并非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也没有虚张声势,发宣言做议论那些套话,孙甘露让每个人物在行动中去展现自己的性格。因为故事的动态性,人物的运动感很强,这仿佛是动作片一样,人物摆脱了静态存在的沉闷,人物的机警、心理活动、智慧以及身手都在行动中透示出来。固然,主要人物我地下党陈千里和敌方叶启年写得相当成功,这俩人一直暗地较量,又有正面交锋,而且还有家国爱恨。叶启年一直认为是陈千里把女儿叶桃引入共产党而潜伏在身边;哪想到实际上是叶桃把陈千里带进组织,引导他走上红色革命道路。叶桃之死与叶启年脱不了干系,虽然并非叶启年直接“大义灭亲”,但他显然怕“家事外扬”。这当然是一个悲剧,本来陈千里和叶桃或许能相爱一生,陈千里会是叶启年的乘龙快婿,但20世纪的酷烈把这些原本可能性的“亲情伦理”,皆转向党国的敌意,变成了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深仇大恨。在中国20世纪的进程中的这些生命和亲情代价,孙甘露隐而不显,含而不露,在追求客观性和紧凑性的同时,略微少了一点反思性——这当然是苛求,红色写作中的反思性是一大难题,人性、个人选择、爱恨情仇,都被特殊的历史情势所决定。个体生命、命运如何揭示和深化,确实是一个难题。但不管如何,孙甘露笔下的女性,叶桃和凌汶虽然着墨不多,但却写得栩栩如生,她们永远带有孙甘露笔下的女性的那种属性,优雅、美丽、坚决,她们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们用行动给20世纪的中国历史写下了革命的红色篇章。
当然,孙甘露的小说最值得称道的永远是他的语言,他是一个始终用语言写作的作家,不管写什么题材,不管年月发生什么变化,他的语言质地不会褪色,这是一个道地的作家的可贵品质。这部小说之所以可以创造出紧凑性和紧张感,人物刻画几笔就神情毕现,根本还是得益于孙甘露的语言。即使去掉了先锋小说的那些绚丽和华美,在简洁质朴中,依然可以感觉到孙甘露的叙述语言的那种洁净、准确、精炼和细致。有语言背书,孙甘露这部小说用《千里江山图》为名,也算是自然天成。传统工笔的精致细腻,荡气回肠的神韵,在孙甘露的精雕细刻的语言中,也显山露水;然而,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的生死酷烈中,它们前后呼应,共同演绎着千年绵延的一个民族的命运。
作者:陈晓明 (文艺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郭超豪
策划:邢晓芳
责任编辑:宣晶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