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特殊的冬春的日子,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很多活下来的人,生命被彻底地改变了。在悲伤的空气中,春天仍如期而至。幸存的人、幸运的人,没有资格缩在痛苦的茧房里让心凋萎。至少还能读书,至少,文学、知识和思想能让我们在残酷的世界中看得更清晰。
人会恨一些东西,是因为他们爱一些东西,有恨,是因为有爱,有爱,所以有灵魂。
这里摘录《米沃什词典》里的两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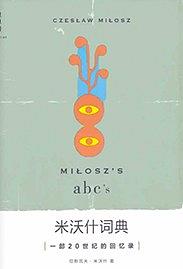
MISFORTUNE(不幸)。我们不能简单地漠视不幸,以为只要否认它的存在就可以安心,因为它的确是存在的。既然无法摆脱它,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选择一种跟它相处的策略。当外敌侵犯蜂窝时,蜜蜂肯定要在蜂窝周围涂一层蜡。唉,这种在入侵者周围涂蜡的劳作必须重复进行,但这是必需的,否则不幸就会来控制我们的所思所感。
无数的人,包括那些早于我们的人和那些与我们同时代的人,都已经认识到或即将认识到不幸。由于不幸的普遍存在,《约伯记》具有永恒的意义。其第一幕把不幸看成是一种惩罚,约伯的朋友们要让他相信的就是这一点。如果他跟他们的争论没有涉及目的论,我会说,他们是对的:不幸的降临是一种报应,一种惩罚。由于我们在遭遇不幸时想到我们的罪,不幸的降临在某种意义上就被证明是正当的。约伯反驳说,他没有罪,这使我们感到惊讶:什么东西使他如此确信自己的美德?不过,那可以被称作《约伯记》第二幕的,是为上帝的辩护。此处的上帝就像一个人,而不是奖励或惩罚的施予者。如果约伯真是无辜的,那么上帝之所以要惩罚他,是因为上帝喜欢那样做。这意味着,我们对正义和非正义的理解并不适用于那个一直指向上帝的指控,那个指控往往被压缩成一声惊呼“为什么?”波舒哀在布道中说,上帝照应着个人和历史,主管着奖励和惩罚。这样的上帝形象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把这一观念扩大到整个宇宙的维度,那么我们对善良的追求就只能靠仁慈的上帝来满足了,上帝不会让数百万的生灵屈从于痛苦和死亡。去创造一个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相像的宇宙并不令人愉快。“为什么我非得要做好事?”上帝问道,“你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想法?”
不幸就是不幸。当你用蜡把它封起来,你还是不能心安理得,因为或许你应该将所有努力和专注都献给它。为了自我辩解,你只能说:“我想活下去。”
TRUTH(真相)。尽管人们攻击有关真相的种种概念,尽管人们再也不相信那种对过去的客观发现的可能性,但大家还在继续热情地写作回忆录,想揭示事情的真相。这迫切的需要是一种证据,表明我们的叙述是基于所谓的事实,而不是屈从于变动不居的观点。大家都知道,同一个事实在两位目击者眼里并不相同,但一个诚实的编年史家自信他的描述千真万确。在此,他的诚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应该尊重这一点,即使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为自己的兴致塑造了事实。更改事实,从而粉饰过去,或掩饰丑陋,这是使观点受到歪曲的最常见的原因。我们常常为故事讲述者的盲目感到惊讶,他自己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最不可信的是政治家的回忆录,因为他们撒谎太多,所以我们很难相信他们的诚意。
当我谈论自己所亲身经历的 20 世纪时,我力图做到诚实。在这方面帮助我的,是我的过错,而不是我的美德。对我而言,这一直就很难选择。我很难宣称自己属于某一方,或者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由于我顺从自己在与同时代人的关系中常像个局外人的这样一种状况,我力图凭直觉去了解对方的理由。如果我具有合作精神,我会取得更大的成功。由此可以推论出:当人们希望宣布某些明确无误的道德判断时,其精神会遭遇相当的困难。即使各种各样的人演绎出各不相同的人生形态,我们仍努力想要了解人生的真相。我们彼此分隔着,但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是中介,被一种我们不太了解的力量驱使着。那种力量就像一条大河的水流。经过它,我们就会变得彼此相似,就会拥有共同的风格和模样。我们自己的真实形象会使我们想到马赛克,组成这马赛克的是一些具有不同的价值和色彩的小石子。
编辑:山鲁佐德
责任编辑: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