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时代周刊》关于阿尔弗雷德·鲍尔的深度报道,揭开了与柏林电影节有关的盲点,一个在二战期间参与迫害电影人的第三帝国技术官僚,战后成功遮掩自己的罪过,一手缔造了一个以反思历史为艺术态度的电影节——历史在此显露它吊诡的面目。
即便没有《德国时代周刊》的考据调查掀起这场风波,“历史”也一直是柏林影展背着的包袱。前任艺术总监科斯里克在任18年,影展主竞赛单元的选片屡次向历史题材和当代争议题材倾斜,被指责政治取舍凌驾于审美。随着科斯里克卸任,业内对夏提安的接任是充满好奇的,关注影展怎样调整选片思路以应对来自圣丹斯影展和奥斯卡颁奖的压力——这三者集中于2月,时间接近,很多片方分身乏术以至于不得不作出非此即彼的取舍。然而,今年主竞赛单元的18部入围影片公布时,来自评论界的最明显的声音是:卸任的科斯里克影响仍在。
前任艺术总监以他多年的强悍风格,为柏林影展的选片视野界定了明确的框架:历史的黑暗地带、当代敏感议题、当代史和历史背景下的被放逐者、历史和现实的互文、女权主义和女性视野。这些元素在今年的竞赛单元中保持着强势。
《亚历山大广场》把阿尔弗雷德·多布林的同名小说改写到当代语境,多布林的原作出版于1929年,写的是那个年代的“当代故事”,后来因为法斯宾德在1980年改编的电视剧而广为人知。新版电影把主角的身份改为西非难民,他被海浪送到欧洲南方的海滩上时,以为美丽新世界将在面前展开,而他辗转流落柏林,混迹于亚历山大广场时,经历梦想屡次破碎的他,看清了欧洲的街头是比黑夜更黑暗的地方。
《删除历史》是把当代故事放到历史的坐标系里,三个互联网深度用户各自陷入孤岛式的绝境,导演从喜剧的情境中捕捉到21世纪的“历史书写”——“向左”“向右”的分歧被数据消解,在技术制造的环形监狱里,数据吞噬身份直到吞噬一切。
《所有死者》把契诃夫的《樱桃园》和《三姐妹》移植到19世纪初、刚刚废除奴隶制的巴西,契诃夫笔下那些生活在俄罗斯外省,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们,成为了可以嵌入任何语境的神话般的原型。
意外与电影节眼下的难题形成呼应、呈现“历史”伦理难题的,是参赛片《列夫·朗道:娜塔莎》。
这是一部可以追溯到2004年的作品,导演的初衷是拍摄一部关于俄罗斯物理学家列夫·朗道的传记片,关于这位196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从1938年到1968年在莫斯科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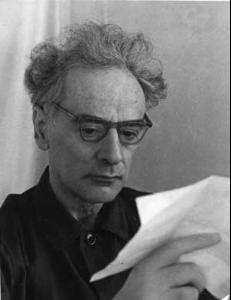
2005年,片方在乌克兰东北哈尔科夫的空旷地区,再造了一个迷你的“1938年的莫斯科”,之后这个项目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起初为了拍摄打造的片场,逐渐成为真人秀的现场,一个当代的、真实的“楚门的世界”,片方声称“超过400名主演和10000名群演的参与者是自愿留在其中,生活在1930-1960年代的莫斯科”。在那个与世隔绝的社区,建筑、人们的穿着、发型和生活用品等都照着俄罗斯在1938-1968年的样子相应地进行更新,这个独立的“社会”专门有一套计算年份的系统。导演把剧情片的拍摄变成了纪实偷拍,从2005年到2011年,整个摄制团队只有三人,他们会在随意漫步时记录下某个人物某个事件,积累了700小时的影像素材,从这些素材中,导演剪辑了4部影片,创造了3个浸没式影院作品。
2014年,戛纳影展艺术总监福茂表达了对《列夫·朗道》的期待,表示“不知道这部电影会走向什么方向”,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与《列夫·朗道》有关的影片并没有入围戛纳。
导演在创作浸没式影院作品时,屡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因为自己的俄裔犹太人身份,希望首演能在柏林。但这个作品在伦理层面的争议性,遭遇德国媒体的集体抵制,最终,浸没式影院作品《列夫·朗道》的于2019年初首演于巴黎。
可以预见《列夫·朗道:娜塔莎》在柏林首映后将引发的争议,它的创作路径、它的呈现方式以及创作者召唤“历史”的姿态,都是越界的。德国女演员汉娜·许古拉曾说过这是她没法看下去的电影,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历史的再现,而是真实的重演,是字面意义的,暴行的卷土重来。”这些影像成了一个特殊的现场,在这里,扮演模糊了生活的边界,模拟成为一种更强悍的现实,随着修辞的约束被解除,历史不再是等待被认清的客体,它无法被切割、被观望,它是当下的一部分——无论电影或影展,要怎样面对这个成为悖论本身的怪物?
作者:山鲁佐德
编辑:周敏娴
责任编辑:柳青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