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修订版)》记录了60多种行将成为历史的老手艺、老行当,用简朴的语言描写了曾经游走在乡土中国大地上的老手艺老行当人的酸甜苦辣、生老病死,将正在渐渐消逝的传统生活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全书从个人记忆切入,通过大量、扎实的实地访谈、田野调查,重现老手艺的彼时彼景。漫画家邓辉华为本书绘制的漫画插图,寥寥数笔,生动传神。此外,修订版在初版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饰润色,每种行当都补充了民谣、民谚等传统文化的内容,并增加了凝练手艺精髓或点破行当辛酸的竹枝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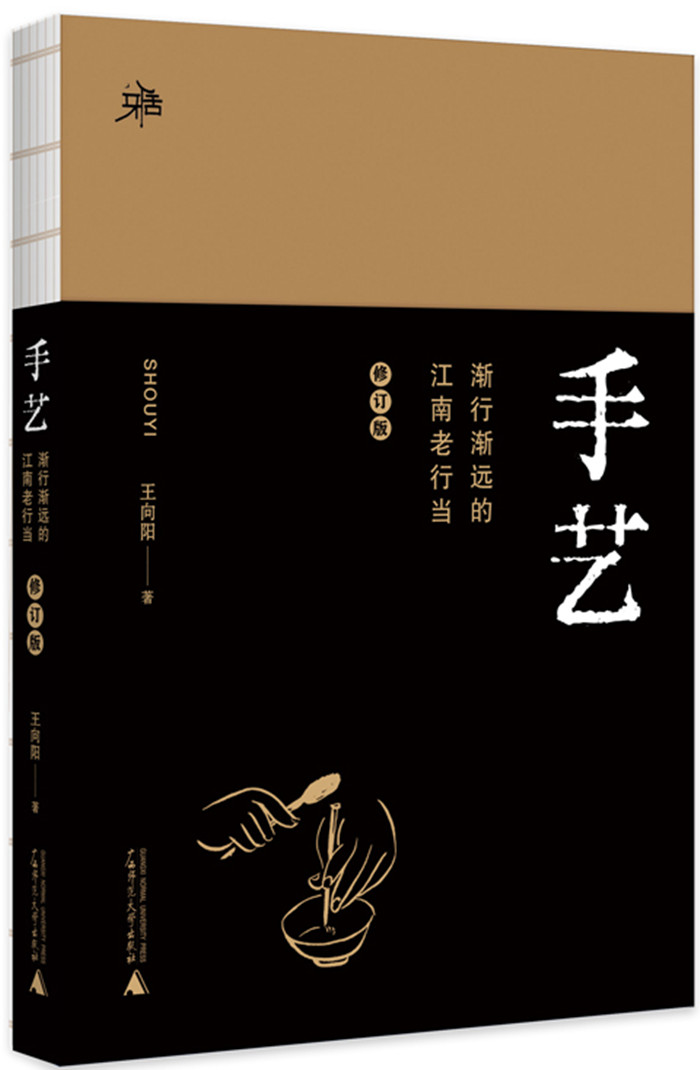
《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修订版)》
王向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烧茶壶砂罐
一只乌鸡桌上栖,客人来了把头低。
寒冬腊月拉坯苦,滴水成冰两手泥。
“卖茶壶哦——卖砂罐哦——”小时候,听到吆喝声由远而近,就看到小商贩肩挑一根长扁担,挂着两只肥大的箩筐,装满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灰陶。
与细腻光洁的瓷器相比,没有上釉的灰陶颜色灰黑,粗犷古朴,有茶壶、砂罐、泥壶、箸筒、盐壶、药罐、火熜钵和香炉等。农家来了客人,主人随手提起桌上的茶壶,倒一碗茶水。家乡有个谜语“婆婆的家里有只乌骨鸡,客人来了爬在桌顶撒尿”,谜底就是茶壶,颜色灰黑,形状像“乌骨鸡”,茶水从茶壶嘴里流出,动作像“撒尿”。在食不果腹的年代,人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吃“铜罐饭,砂罐肉”。铜罐密封,烧出来的饭香气扑鼻;砂罐受热均匀,熬出来的肉原汁原味。另外,用药罐煎药,药性稳定,为金属器皿所不及。
我家的药罐不常煎药,倒常煮饭。五岁之前,我跟年过七旬的爷爷奶奶同灶,爱吃用药罐炖出来的烂饭,俗称霉霉饭。每次烧饭,奶奶在药罐里倒一盏米,加满清水,盖上盖子,放进灶膛,在柴火中烧开,滚水溢出,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等灶膛的明火熄灭,剩余的炭火煲着药罐,把里面的烂饭焖熟。
小商贩上门叫卖的灰陶,产自二十里外大许公社茶壶窑村。早在清朝道光年间,一对湖广(今湖北、湖南)地区的罗姓兄弟来到浦江,定居在岩头牛轭歪村,以烧灰陶为生。后来,弟弟迁居到大许中埂村,建起茶壶窑,以此为村名。
当初,茶壶窑村的罗姓人家立下规矩,烧灰陶的手艺“只教媳妇不教囡”。后来,朱、于两姓先后迁入,拜罗姓人家为师,破了老规矩。要学好这门手艺,绝非一日之功,要“三年徒弟,三年半作,三年伙计”。
到了1958年,15岁的罗兴满小学毕业,跟着爹爹学烧灰陶,成为第六代传人。当时,正好赶上“大跃进”,城乡处处大办食堂,急需大批炊具,能蒸半斤、四两米的蒸饭壶很畅销,一订就是五百、一千个。
烧制灰陶,经取土、粉碎、和泥、拉坯、晾干、烧制等工序。挖泥时,先剔除表层的浮泥,再挖掉中层的隔泥,然后选用底层的黏土,最后将土地恢复原状,不误耕种。烧灰陶的黏土比烧砖瓦的黏土要求更高,须色青、质细、柔软、纯净。和泥时,黏性很强,用脚踩,用木棍打,用手揉;拉坯时,用熟泥在陶轮上拉出各种各样的泥坯,组成器皿,全靠手感和经验,“所有生活一手落”,“只会做,不会修”不行,“只会做罐,不会做盖”也不行。一名熟练的窑工,一天能做百来件泥坯。
整天与黏土打交道,窑工双手干燥,皮肤开裂。不能洗手,只能用破渔网擦手。等破渔网上的泥土干透,双手一搓,就掉落了。等全天的生活都做好了,才用清水洗手。
灰陶要会做,更要会烧。茶壶窑村的茶壶窑高两米六,外围直径四米,用大石头垒就,呈圆柱形,内膛直径一米五,用砖砌成,呈椭圆形,分上下两层:上层装陶,下层烧火。烧一两个小时的焙火(用微火烘),两三个小时的小火,七八个小时的中火,三四个小时的大火,一共十三四个小时。看窑中的泥坯从黑色变成红色,再变成鲜白色,就可闭窑。然后拿洋油火把在茶壶窑外部检查,如果“轰”的一下烧起来,说明漏气,得用烂泥糊好,否则烧出来的灰陶就会黄胖。灰陶烧得好,不穿孔、不变形;烧不足,颜色黄胖,质地疏松;烧得过头,歪瓜裂枣,不成样子。
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年代,窑工烧窑心里没底,只有祈求窑神保佑。每年正月烧火之前,都要祭拜窑神。祭品用一块长条形的刀头肉,插着一把菜刀,放着两支筷子,还有一块豆腐和一盏米。窑工烧纸焚香,双手合十,虔诚地拜上三拜,嘴里念念有词:“请窑神保佑我们,泥坯进去,青货出来。”
在20世纪60年代,烧一窑灰陶有上千件,按大小定价:一根柄茶壶、大菜壶、蛋瓶、箸筒算一件,卖九分钱;火熜钵、小菜壶、莲子罐、香炉、灯盏头算半件,卖四分五厘钱;茶壶、大砂罐算一件半,卖一角三分五厘钱。兴满师一年要烧十窑灰陶,一窑价值五六十元钱,毛收入五六百元钱。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乡人爱用火熜取暖,人手一只,须臾不离。从八月份开始,茶壶窑村开始烧火熜钵,四分五厘一只,卖给篾匠。篾匠在火熜钵外编一层细篾,装上手柄,做成完整的火熜,身价倍增,卖三角钱一只。
一窑灰陶烧好后,大小搭配,分成五份或者十份,以抓阄的方式,一次性批发给外村的小商贩。小商贩来自七里公社七里村、周宅村和大许公社莲塘五份头村,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县各地和邻近的义乌、诸暨、桐庐、建德、兰溪等县。只有到了梅雨天和腊月底,窑工才挑着灰陶上门兜售。
卖灰陶是一门无本生意,不用垫脚。小商贩以翻番的价格把灰陶卖完后,再来窑上结账。1949年前,都是记账赊销,等到端午、中秋、春节三个节日,一起结清。有的穷人身无分文,连箩筐也买不起,先向兴满师的爹爹借两个,挑着灰陶上门兜售,等卖掉了,再来结货款,置办两个箩筐。大多数小商贩讲诚信、重然诺,也有个别人卖了灰陶,不来结账。兴满师的爹爹总是宽厚地说:“骗么骗一点,钱下辈子也要用,子孙后代会好一点。”
别看烧灰陶是乌泥变黄金的行当,但窑工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汗水。在大集体年代,他们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烧灰陶,日夜不歇。到了过年之前的十一、十二月,正是销售旺季,不论落雪落雨,都要烧制。早上起来和泥,天寒地冻,冷得要命,在身边放一个火炉,烧一壶热水,实在吃不消,双手浸在热水里暖和一下,再接着干。到了后半夜,滴水成冰,如果发现茶壶窑漏气,就用烂泥把漏洞糊好,刺骨冰冷。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土匪恶霸横行乡里,勤劳殷实的茶壶窑村民备受欺负。有一次,兴满师的爹爹接到土匪发来的一张红帖,勒索一千斤大米。土匪不要实物,大米沉重,不易搬运;也不要钞票,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最后以三捆五盒洋纱替代一千斤大米。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城乡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茶壶窑村不是世外桃源,大许公社以窑工早晚烧制灰陶影响白天集体劳动为由,将陶轮等制陶工具没收了。
改革开放后,茶壶窑村又可以光明正大地烧制灰陶了。可好景不长,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日用器具讲究了,爱买光洁的瓷器,粗糙的灰陶销路越来越差。到了1987年,兴满师告别传承了六代的老行当,改行从事搬运吊装行业。
到了2020年,茶壶窑村只剩下六位老人还能烧灰陶,这门古老的手艺濒临失传。
作者:王向阳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