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三十年前,张艺谋处女座《红高粱》横空出世,拿下柏林金熊,震惊世界影坛。
“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
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捧红了巩俐,成就了张艺谋,也让莫言爆得大名。当年的大街小巷上,人们走着走着,就会吼一嗓子“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啊头……”
如今的80后、90后影迷们无缘得见当年一票难求的盛况,但现在有机会弥补遗憾了。从10月12日起,由西影集团重新修复剪辑的高清版《红高粱》将在全国近千家影院重新上映。

高粱地里,莫言这样走来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中,莫言的写作像推土机一样强劲有力,他翻耕过的田野,散发出高粱酒的香气、青草的香气和饽饽的香气。
从娘胎里落到尘土上,嗷嗷成长,莫言的身份是不折不扣的农民。他在土里生,在土里长,他对土地的爱恋和憎恨同样强烈。他对自己家乡充满了逃离的渴望,真正离开这片土地后,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割断对家乡的依恋。

小时候生存环境很恶劣,但是并非一切都不堪回首。对于儿童来说,在探索中饱食终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莫言这样描述自己的诞生:1955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
从大街上扫来尘土垫在产妇的身体下,这种习俗似乎暗示着人的生命从土中而来,因土而生。同时,也昭告着这样的事实:人也是一种卑贱如土的生灵。惟其卑贱,才有野草般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莫言生不逢时。当他开始长身体需要大量的食物和营养时,遇到了饥寒交迫的粮食大匮乏。乡村的孩子变成了啮齿动物。

▲莫言(左)小时候与堂姐
少年莫言和同龄猴孩们的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他们大冷天的还光着屁股像小狗一样四处游荡。他们的身上没有多少肌肉,胳膊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肚子薄得透明,里面的肠子蠢蠢欲动,肚皮却大得像一个大水罐子。
许多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他们的美味:
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那时候我们都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东西。
莫言神乎其神地说,他的一个儿时伙伴后来当上了电工,他的工具袋里既没有钳子也没有刀子,像铅笔那样粗的钢丝他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咬断,别的电工用刀子和钳子才能完成的工作,他用牙齿就可以完成了。当一种需求上升为人类的基本和终极追求时,为了适应这种需求,人们的特殊的能力就会不断地被强化。啮齿能力,就在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食物的过程中,得到了突出的发展。

▲《红高粱》中,高粱地的镜头
莫言小时候生存环境很恶劣,但是并非一切都不堪回首。对于儿童来说,在探索中饱食终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少年时代的莫言和伙伴们的食物探索过程,继续向着匪夷所思的境界进发。
1961年的春天,莫言刚刚上小学一年级,大栏村村立小学的校园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莫言他们这些小孩那时候孤陋寡闻,没见过煤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经过充分进化的牙齿在这时发挥了探索世界奥秘的主导性作用。一个大胆的小孩子试探地拿起一块,放到嘴里咬了一口。他咯嘣咯嘣地吃了起来,就像是在品尝一块珍贵的饼干,表情享受,香甜无比。
其他孩子得到了启示,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
我感到那煤块越嚼越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村子里的大人们也扑上来吃,学校里的校长出来制止,于是人们就开始哄抢。
这种珍贵的历史镜头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可能出现。
第一次割麦子,手艺生疏,心慌脚乱,割得慢不说,麦茬子留得还特别长,麦穗落得到处都是
1966年莫言辍学,1973年莫言通过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会计的三叔的关系走后门在厂里当上了季节工——其实就是临时工,最早的民工——这期间有七年的漫长岁月,少年莫言从十一岁到十八岁,都是一个地地道道、彻彻底底的农民,又或者说,是一个不称职的、一直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公社小社员。他先放了两年牛羊,接着下地割麦,又接着去参加挖河修桥的劳动。从十一岁小学毕业开始,他就用自己的双脚和双手,在丈量和熟悉着这块生养自己的土地。
莫言的家乡是三个县交界的地区,交通闭塞,地广人稀。村子外边是一望无际的洼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
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在田野里与牛为伴。
我对牛的了解甚至胜过了我对人的了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们心里想什么。
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里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原野里,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牛安详地吃草,根本不理我。
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白云缓慢地移动,好像它们是一些懒洋洋的大汉。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不理我。
天上有许多鸟儿,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叫得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与鸟儿们交流,但是它们也很忙,它们也不理睬我。
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满了悲伤的感情。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非。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许多美妙的念头纷至沓来。
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么叫爱情,也理解什么叫善良。
然后我学会了自言自语。那时候我真是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而且合辙压韵。

这种和自然界交流的方式,充分地开拓了莫言的阅读视野。这种开拓,显然也不是莫言自己要求的,而是天赐的,是一种命中注定要让他的各种感官得到充分开掘的基础训练。
莫言第一次割麦子,手艺生疏,心慌脚乱,割得慢不说,麦茬子留得还特别长,麦穗落得到处都是,遭到了生产队会计的嘲讽和批评,说他这不是搞生产,而是搞破坏。
四叔只好不让他割麦,让他到割麦的大人后边捡麦穗,还是个边角料的活。这件事情让小社员莫言非常委屈,心里也难过。
晚上回家,他向爷爷诉苦。这位方圆几十里地鼎鼎大名、死活不肯加入生产队的庄稼老把式听了,第二天不动声色地来到了田头。生产队那些后辈油子们大多听闻过管遵义老人家的光辉历史,见他来了都心里紧张。从前请他到田边指导他都不爱搭理,这回儿现了真身了。
他老人家原来在自留地里干活,好多人都来参观学习,他的割麦成了一种表演,很潇洒,也很得意。莫言说他的镰刀磨得好,看不到手和麦子怎么接触,后面一个麦穗都不掉,麦茬子贴着地面,后面是一排列队士兵似的麦个子。老人家割麦时顺手把麦子一揽打个活结,成一个漂亮的麦个子,整整齐齐地躺在后面,那活确实漂亮。不像低手割麦,像拉羊屎似的,掉得满地都是麦子,后面还要人捡麦穗。

莫言的爷爷把干活上升到了一种劳动美学的高度。莫言对自己爷爷的崇拜,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神奇,这位仁慈的老者成为他进入自己故乡的最为有效的捷径。
七年不是一瞬,小社员莫言在农村里劳作的苦与乐,显然一言难尽。那时候的劳动更多的当然是苦,只能苦中作乐。
那时候的劳动,是干一个小时歇一袋烟工夫。歇着时老人们就神侃,胡天胡地,古今中外,大多是乱说和瞎掰,半句离不开吃的喝的,每个人都能说得神乎其神。莫言邻居有个单家,解放前是开烧酒作坊的——这里面的一些内容,显然被莫言演绎成了《红高粱家族》里烧酒作坊主单秀才单廷秀的故事——他们家有一个儿子,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过书,毕业后在济南工作。
他也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

这位中文系的毕业生对作家生涯非常神往,常常说一些关于作家的演义。他说济南还有一个作家,因为写作有钱,生活非常腐败,一天三顿吃大白菜肥肉馅饺子。
在那样一个贫困的年代,可想而知莫言对饺子是多么的有感情了,更何况是大白菜肥肉馅的饺子。莫言听得垂涎欲滴。
日后,莫言在多篇散文和演讲中,都提到过“一天能吃上三顿饺子”的故事。他一本正经地说着自己小时候的糗事,说自己之所以想当一个作家,就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就是想娶石匠的漂亮女儿当老婆。
把一前一后两个小说杂揉到一起,又亲自送到了编辑部,就这样,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了
根据莫言在《漫长的文学梦》里的说法,他的创作应该从1978年开始,更早期当然可以追溯到1973年十八岁的莫言在胶莱河挖泥时创作的《胶莱河畔》,然而那次创作没有继续下去,不形成整体性的创作阶段,所以还算不上真正的创作生涯。

▲莫言小学时的作文本,用的还是本名“管谟业”
在这段时间里,莫言写了不少习作。
后来我调到保定,为了解决提干问题,当了政治教员。因基础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书。文学的事就暂时放下了。一年后,我把那几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课不用拿讲稿了,文学梦便死灰复燃。我写了许多,专找那些地区级的小刊物投寄。
终于,1981年秋天,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莲池》发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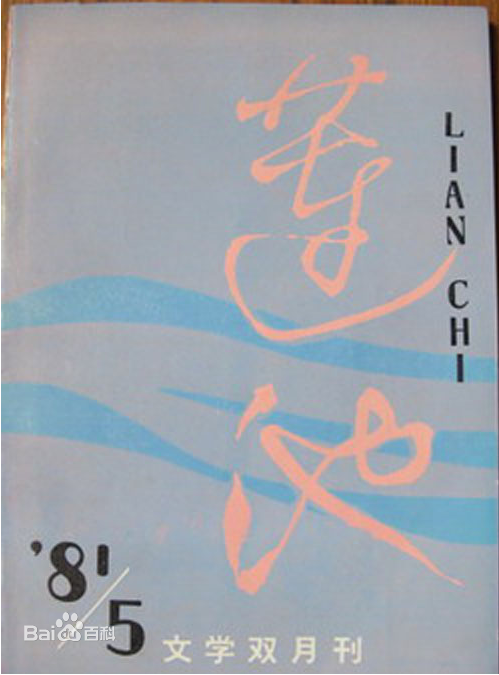
当时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火爆全国,莫言想必也受到了影响,于是雄心勃勃地想写一部话剧,一旦发表就一炮打响,从此名扬天下。
他在话剧创作上遭受了打击,写话剧的心愿,要到写《我们的荆轲》时才能了却。
《春夜雨霏霏》的发表还有一些故事:
1979年秋天,我从渤海湾调到狼牙山下,在一个训练大队里担任政治教员,因为久久不能提干,前途渺茫,精神苦闷,便拿起笔来写小说。写出来就近往《莲池》寄。寄过去,退回来,再寄过去,又退回来。终于,有一天,收到了《莲池》的一封信。
由此可见,在那段时间里,莫言确实写了不少的练习作品。这些习作都或者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得到编辑的青睐,他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就处理掉了。直到其中一篇小说得到了编辑的来信。这封回信上,一名编辑希望莫言能去编辑部谈谈。

莫言把这封信翻来覆去地看,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就搭上长途汽车赶到保定市,按着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莲池》编辑部:
进门前我紧张得要命,双手不停地流汗。进了门就转着圈敬礼,然后把那封信拿出来。一个中年编辑看了信,说:“你等一下吧,老毛家远,还没到。”我就坐在一把木椅上等着,偷眼看着那几个编辑在埋头处理稿子,感到他们的工作庄严得要命。同时我还看到他们每个人面前都堆着大摞稿子,于是知道爱好文学的人很多。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哈着腰进了门。
方才看过我的信的那个编辑说:“老毛,你的作者。”
就这样,我见到了我永远不敢忘记的毛兆晃老师。
毛兆晃老师五十多岁,个子很高,人很瘦,穿一身空空荡荡的、油渍麻花的中山装,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烟臭。他把莫言让到桌前,简单地问了一下莫言的创作情况,然后把莫言投的那篇稿子拿出来,说小说有一定基础,希望莫言回去之后改一改。
说完了稿子,他问我喝不喝水,我说不喝,然后我就走了。

莫言大闺女上轿头一回走进心目中神圣的文学杂志编辑部,心里紧张和激动,都是很正常的。凡事都有第一次,毛兆晃老师给他第一次的肯定,对他来说相当于在自己的漫长文学创作生涯中走出了第一步,也相当于一个打毛衣的姑娘,给自己的棒针打上了第一个结。有了第一个结,后面就好办了。
莫言回到部队后,感到不好改,干脆新写一个,又几十里迢迢地亲自送到编辑部给毛老师审阅。毛老师一目十行地看了,说还不如第一篇好呢。他的话让莫言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莫言没有气馁,他对毛老师表决心说自己愿意改,保证能够改好,然后他又坐上长途汽车回去了。
回到部队里,莫言考虑了很久,把一前一后两个小说杂揉到一起,又亲自送到了编辑部。过了一段时间,毛兆晃老师给莫言来了一封信,说这一次改得不错,刊物决定要用了。
就这样,莫言在《莲池》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
一天中午,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在楼下叫莫言。叫他的人正是张艺谋

▲电影《红高粱》拍摄时期的旧照。从左至右分别为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莫言与张艺谋的结合,是当时最为经典的小说与电影双赢的壮观场面。
那是1986年:
我当时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那年暑假,我正在赶写一部中篇小说,中午有人在楼道里喊我:“莫言!莫言!”
我出来一看,一个穿着破汗衫、剃着光头、脸黑得像煤炭的人,手里提着一只凉鞋,是用废轮胎胶布缝成的凉鞋,也就是特别简陋的那种,他的一只凉鞋的带子在公共汽车上被踩断了。
他说他是张艺谋,他看好了《红高粱》,想当导演。我对张艺谋做摄影师拍摄的电影很感兴趣,他作为演员、摄影已经很有名了。我们谈了统共不到10分钟。……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非但无关,我还要欢呼你的好勇气。
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用张艺谋的说法,小说驮着电影走。小说界的莫言、电影界的张艺谋,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各方面趋向成熟,有阅历、有经验也有激情。
如今享尽了荣华富贵的导演张艺谋,那时“手里提着一只凉鞋”,可谓是创业之时事事艰,惟有雄心可凌云。
写出了中篇小说《红高粱》之后的莫言,也处在一种疯魔的状态,根本就无法顾及其他,只是拚命地写小说,要一股脑地把胸中的“不平”之气吐出来,不一定是风吹如兰,也可以倒海排山。
那个时候人们的想法比较简单,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千万窟窍。小说改编版权,不过是八百块钱。在那个时候,这笔钱跟小说稿费比起来,一点都不显得特殊,所以,小说家有资格跟电影导演平起平坐。
这跟后来电影慢慢地变成了老大,小说变成了老二的情况完全不同。

莫言说,他一开头不想参加改编,但张艺谋希望他参加编剧,因为牵扯到一些民俗啊之类的东西。编剧总共是三个人,一个是陈剑雨,一个是朱伟,署名最后加上莫言。莫言回忆说,稿子是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执笔的,分上下集:
1987年,我在高密,张艺谋把他的定稿拿给我看,定稿跟我们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惊讶。这点儿东西,几十个场景、几十个细节就能拍成电影?
后来,我明白了,电影不需要太多的东西。
比如“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几句话,在电影里,就“颠”了5分钟。
这个电影拍出来后,我看样片,确实感到一种震撼,它完全给人一种崭新的视觉形象。应该说,在视觉上、色彩运用上,营造出这么强烈氛围的,《红高粱》是新中国电影第一部。
它很快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得了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A级电影节上得奖。
电影的影响确实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但当1988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电影《红高粱》在拍摄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两个当鬼子的演员,化了装,到高粱地里解手,有个老汉正在拔草,抬头一看,吓得脸煞白,扔下筐就跑:“俺那娘哎!怎么鬼子又来了!”
内容摘编自《莫言评传》,叶开著,河南文艺出版社
编辑制作:徐璐明
责任编辑:邵岭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