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托宾小说《布鲁克林》改编的同名电影剧照。(资料照片)
托宾说,写作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缔结的想象力契约,但想象无法翻越生活的边界。在《布鲁克林》里,他写爱丽丝的故事,是把自己的感受给了她,她的遗憾、悔恨和漂泊感,是他的,她没能厮守的亲情、错过的爱情,也是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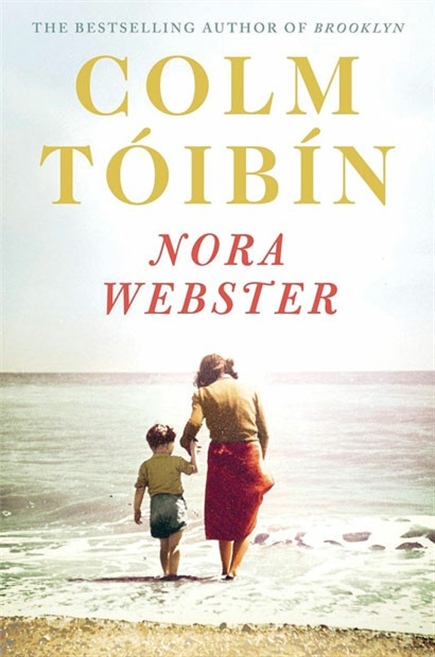
托宾小说《诺拉·韦伯斯特》封面。 (资料照片)
前天晚上,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风雨兼程地赶到复旦,因为雨夜糟糕的交通,他迟到了,大步流星地走进教室,豪迈地脱去羽绒外套,豪迈地开始他的演讲。他用宏亮的嗓音讲述故乡,一个灰暗乏味的爱尔兰海边小镇,如何通过他的想象成为另一个暗流汹涌的文学世界,和弥漫在他小说里伤感失落的情绪不同,他敞亮的幽默感照亮了那个寒冷多雨的冬夜。
私下的场合,托宾仍然是我们从他的文字里想象勾勒过的模样,敏感,彷徨,迂回,他是一个坦诚的作者,试图诚实地交出自己,但他不相信斩钉截铁的判断,警惕着不愿作出任何太轻易的结论,坦率和纠结在他身上和平共处。
托宾的长篇小说《大师》为他赢来最多文学声誉,他在创作《诺拉·韦伯斯特》的间歇里,写出《布鲁克林》这个小长篇,因为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让他从一个在文学专业领域被高度评价的“语言大师”成为亲民的畅销作者。他是个高产的作家,但他的写作总能在这三部长篇里找到感情的落点。《大师》的原型亨利·詹姆斯是他的文学导师,他从詹姆斯那里学到写作中最重要的一课,写人和人性的暧昧与不确定。漂泊无依的失落感支配了他的写作,就像《布鲁克林》的爱丽丝,是故乡和异乡之间找不到靠岸处的局外人。至于《诺拉·韦伯斯特》,是他开始写作时就想写、却迟迟落笔,用了漫长数十年写成的一部“生命之作”,当他坐在我的面前,谈作家,谈作品,所有的话题总会蜿蜒地回到他的故乡,他说:“40年来我在写作的道路上风雨兼程,是为了这一刻,我能有勇气和自信回到老家。”
小说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签订的想象力契约
一个多月前,电影《布鲁克林》在爱尔兰东南沿海的恩尼斯科西首映。“你能想象么,那个只有16000人的小镇里没有电影院,放映场所是临时布置的,镇上的人都来了,穿着他们最好、最正式的礼服,看场电影这么平常的事,变成了一桩隆重的仪式。”
那里是托宾的故乡,有灰色的天,灰色的海,漫长的海岸线空旷寂寥,天气和食物都很糟糕。在20岁以前,托宾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乏味悲伤的地方,没有壮丽的传奇,也不可能产生宏大的作品。他买了一张去巴塞罗纳的单程票,迫不及待地离开,把平凡的小人物和琐碎的生活留在身后。“我要写宏大的角色,我要写壮烈的悲伤和喜悦,我要写奇绝壮观的故事,写大喜大悲、颠沛流离的命运。”在地中海的阳光和美食包围中,他度过人生中第一段没有阴翳的快乐时光,开始构思一部野心勃勃的杰作,他想象留在爱尔兰灰色天空下的母亲度过了一段“不可能的人生”:她逃离家庭,投奔地中海的阳光和自由,展开了波西米亚艺术家放浪形骸的一生,有烟有酒,有爱有性,还有创作。可是当他坐到书桌前,试图为母亲的形象和她所在的环境画出速写,他面对空白的稿纸,闭上双眼,看到的第一个画面是乌云浓厚的天空,冰冷翻滚的海浪,空旷的海岸上,母亲孑然一身。他将用40年的文学跋涉,去积攒勇气和能力面对这幅萧瑟悲伤的画面。
但是在那个瞬间,23岁的他明白了,他无处可逃,他所有的想象终将回到山和海的那边,一个多雨、凄凉、沉闷的海边小镇。后来,他走了很远的路,经历了感情和生活的双重冒险,也想象过许多种人生,但他的文学想象和他真切的感情,只能在故乡落脚。从他开始写作的一刹那,他挣扎在两个平行世界之间的漂浮地带,一边是故乡,另一边是他乡,一边是平淡无奇的现实,另一边是万花筒般的虚构。
12岁那年,托宾的父亲去世,这是他生命中遭遇的第一次重大变故,塑造了他的性格,也为《布鲁克林》埋下伏笔。那时,镇上的主妇们来他家吊唁,她们坐在一起说闲话,其中有个唠叨的太太一直在说“女儿去了布鲁克林”。40年后,托宾在德克萨斯州教创意写作课程,在那个干旱炎热的地方,他陷入多愁善感的思乡情绪,少年时无意听到的那些闲话在这时潜入脑海。于是,在一个远离雨水和大海的地方,他开始想象一个爱尔兰姑娘孤身移民纽约,独自在布鲁克林生活、奋斗,她的离开和回归都是痛苦的,她在他乡没有真正意义的归宿,在故乡又成异乡人。
托宾说,写作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缔结的想象力契约,但想象无法翻越生活的边界。在《布鲁克林》里,他写爱丽丝的故事,是把自己的感受给了她,她的遗憾、悔恨和漂泊感,是他的,她没能厮守的亲情、错过的爱情,也是他的。“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思乡的主题,第一次思考故乡对我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写失落的人和失落的感情,自从父亲死去的那一刻,无处可归的失落感就伴随着我,它塑造了我,主宰了我迄今为止的写作,也许,我的一生都将和这份失落感相伴随。”
最伟大的戏剧存在于寻常的细节中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认为,《布鲁克林》可以和亨利·詹姆斯的《贵妇画像》相提并论。詹姆斯正是托宾最欣赏的作家。托宾不止一次地强调,除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给了他最大影响的是美国作家詹姆斯,在詹姆斯的所有作品中,他最爱的是《贵妇画像》和《华盛顿广场》。他这样评价他的文学偶像:“他有宽广的同情心、卓越的文采。我喜欢他戏剧化地处理道德话题,又关注感官和时髦。我喜欢他在写作中微言大义,晦暗含蓄,他拒绝让读者妄下判断。他对人类关系中动机的奇特和情感的摇摆性有着最深刻的理解。”他在詹姆斯创作的人物身上,能看到生活的全部:“纯粹的善或纯粹的恶是非生活也非文学的。小说处理的命题是人和人性的不确定,人是暧昧的,生活是含混的,没有是非分明的善恶。戏剧性不从大是大非大悲大喜中来,它根植于每一处细微的不明确。只有宗教意义上的奇迹是明确的,而生活和文学的领域里没有奇迹,小说的本质是一次缓慢的旅行。”
这也是他不愿对比小说《布鲁克林》和电影版的原因。他肯定了电影的努力,对女主角西尔斯·罗南赞不绝口,认为这个年轻女孩演出了他写作中的精髓。可是,“电影和小说太不同了,电影是直观的,导演用一个画面就能解决我写了十几页的内容。”他坚持以试探的、放慢的步调去接近人物的内在,外部世界再壮阔,也不及心底的波澜。在他的笔下,布鲁克林虽然和曼哈顿只有几站地铁的距离,但曼哈顿的灯火辉煌离爱丽丝很远,1950年代存在于纽约空气里的躁动离这个爱尔兰女孩很远,蠢蠢欲动的民权运动、嬉皮士精神和酝酿中的大转折,统统隐在虚焦的背景里,一个在异乡打拼的女孩生活圈是有限的,只有小出租屋、打工的店里、夜校和同乡会。托宾毫不犹豫地发表他的宣言:“外部世界当然参与塑造了一个人的生活甚至人格,但我感兴趣的是关上房门以后的家庭内部关系,我只想从人的本身出发去写一点东西,写人的脆弱和渴望。”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宾对毕飞宇的《玉米》赞不绝口。“三姐妹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动乱的年代里,可是他把外部世界悬置了,细致地写姐妹之间的关系,她们对男人的态度,对身体的关注和焦虑,以及家庭内部对权力的争夺。当然可以认为这是巨大的隐喻,可是他把琐碎的细节写得多么生动。”他说,不是外部戏剧塑造了人,相反,人的内在才是最丰富的戏剧。当他面对空白的稿纸,在想象中接近他的人物时,他有时会想到莎士比亚,因为“他多么出色地描写了人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世纪的文学只处理人和上帝的关系,直到莎士比亚的出现,他调转了文学的船头,写剥离了神性色彩的人,写与神无关的人间的关系”。他反复地重读《哈姆雷特》,着迷的却不是命运的悲剧,不是善和流血之间的悖论,而是哈姆雷特和母亲的关系,最本能也最无可逃避的一组人物关系。
对托宾来说,母亲的形象和母与子的关系,这个命题是把他推向写作的原动力,也是长久以来驱赶他的幽灵,在詹姆斯和莎士比亚的庇佑下,经历《母与子》和《布鲁克林》以及更多艰难的跋涉,他写下《诺拉·韦伯斯特》这个标题,回到23岁那年闭上眼睛看到的画面:一无所有的母亲孑然地面对灰色的海浪,她没有经历传奇,她的生命里没有过地中海的热烈阳光和阳光下的女性自由与解放,她就在一个乏味的小镇,度过了平凡妇人含辛茹苦的一生。
就这样,托宾松开防线,让小镇的灰色进入故事,他在晦暗中寻找力量:“要回归一个没有色彩的小地方,是需要勇气的,但我回来了,因为40年后的我明白,伟大的戏剧存在于寻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