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静默之身——残障人士的不平凡世界》,[美]罗伯特·F·墨菲 著 邢海燕译 责任编辑:储德天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2年8月出版
【导读】墨菲教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知名的人类学教授,1972年卸下系主任后罹患脊髓肿痛而坐上了轮椅,但他依然坚持用民族志的方式记录了自己从健全人到残疾人的全部过程和心路历程,在1987年出版了《静默之身——残障人士的不平凡世界》(The Body Silent),他不仅为残障人士代言,也从人类学家角度,对美国社会制度、政策和健康人给以残障人士的公然敌意给予批判,并鼓励所有人对生命充满珍惜和敬畏。上海教育出版社于日前出版中译本,获授权编摘全书概要。据中国残联统计,截至2022年,中国有8500万残疾人,占总人口的6.2%,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事业正在得到全方位的提升,制度优势正在显现。
墨菲去世的消息在美国报纸刊发刊发,其影响了很多残障人士
对残障的研究是一扇独特的窗口,从中可以看到个人与社会的斗争,因为残疾人不是一个特殊群体,而是人类状况的隐喻。残障可以展现出人性赤裸裸的本质。
手术失败的被独立和隔离让我正视现实:把死亡当作生命的礼物
我和其他无数人一样,在手术后的恢复过程中感受到的自我更新,是心理和社会过程中一个极其正常的方面。我重生了,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上。我的抑郁因疾病的治愈而消解了,我的身心再次变得完整了。真实的世界是我们工作和繁衍的地方,也是我们必须永远回归的地方。实际上,在仅仅五天后,我就经历了严重的病情复发问题,从自己的手术引起的阈限状态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也就是在这几个月里,我开始认真思考死亡,尽管这已不是第一次。我接受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死亡不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存在状态,而是一无所有。我对死亡的沉思,直接源自我在轮椅上与世隔绝的生活,这给我带来被隔离和孤立的感觉。
人类学使我成为对人类一切事物的“窥视者”(voyeur),并使我认识到它们难以捉摸的美丽和稍纵即逝。活着就足够有趣,我决定重新融入这个世界。我对待生命和生活的态度在生病期间发生了改变。我开始把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每一年都当作一份礼物。从那时起,我开始活在当下。每一天都是我一生的事业,每一个生日都是一个奇迹。我推测我的情况一直会恶化,死亡会作为一种礼物而到来,因此我不再害怕死亡并把它当作老朋友。

回到母校接受教学奖:宛如重新融入大学的“通过仪式”
我第一次出门是在今年3月,当时我获得了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教学奖。这个奖在我康复期的关键时刻颁发,它直接影响了我在最脆弱时期的心理变化。
这顿晚宴也是我重新融入社会的一次机会,它似乎与某种仪式有关。确实起到了“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的作用。按阿诺德·范·盖纳普 的术语来说,“通过仪式”是指那些仪式场合的称呼,标志着一个人从一种社会身份向另一种社会身份的转变。从男孩到男人,从女孩到女人;从单身到结婚,从生到死,而我的仪式见证了我作为一个残障人士在公共场合的再度出现。在这样的活动中,一如既往地会有个简单的招待会,每个人都在聚会中边吃边聊,参与者都是我当教授时有过互动的人。在场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学院院长,哥大所有的人类学者,以及很多研究生和本科生。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出席了晚宴。到场的人很多,观众的反应甚至比预期的还要热烈。
我很快意识到,在这场颁奖会上,与其说我作为一名教师被称赞,不如说我作为一名幸存者被报以欢呼。无论如何,大家的情感是真诚的,我再次感到自己融入了大学。虽然我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这场仪式性的聚会上,我一见到过去的同事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就得到极大缓解。然而我也意识到,绝不是所有的仪式都能消除我新身份的污名化。
早期著作《丛林中的女人们》和静默之身》英文版封面(右)
成为轮椅人:因身体受限而失去部分自我,自尊丧失是心性之“癌”
从第一次诊断出肿瘤,到开始轮椅生活的这段时间,我越发意识到我失去的不仅是健全的双腿,还失去了自我的一部分。不仅人们对待我的方式不同了,更重要的是我对自己的感觉也不同了。尽管有许多亲朋好友的强力支持,我依然感到孤独与隔阂。甚至更糟糕的是,我过去曾有的一切都在逐渐减少。这对于一个从贫穷的孩子摸爬滚打到站稳脚跟,走向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来说,尤其令人恐惧。
身体受损的人与基本健康的人之间的关系很有问题。的确,部分是由于健康者的执拗、偏见、糊涂等,但却不能草率地归咎于此。残障人士也有可能因身体机能受损而误解个中含义。更为复杂的是,残障人士也是带着曲解的视角进入社交舞台的。残障人士不仅是身体发生了改变,他们对自己、对外部世界的人和物的看法也发生了深刻转变。他们经历了一场变形记,他们的意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与残疾有关的所有心理综合征中,最普遍也最具破坏性的是自尊的根本丧失。这种自我受损感的习得,被欧文·戈夫曼称之为“污名(stigma)”或“受损身份”。在我最初坐轮椅的那几个月里,这种丧失感愈来愈大。退缩只会更加损害残障人士的主观情感,进一步降低他的自我价值,情绪进而表现为羞愧。
残障人士的心灵发生了转变,由社会的冗余变成了一种准人类的东西。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巧妙地从社会的中心地带转移到了边缘地带。我获得了一个取决于我身体缺陷的新身份,这要么损害了我先前对人格的要求,要么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先前对人格的要求。在我中年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低能儿,这是大多数残障人士的命运。他们受到身体疾病的折磨,这种疾病转而成为心性上的“癌症”,由此社会关系也会出现病态。他们在世界上生存的基本条件发生了转变,他们在本地做了异乡人,甚至成了流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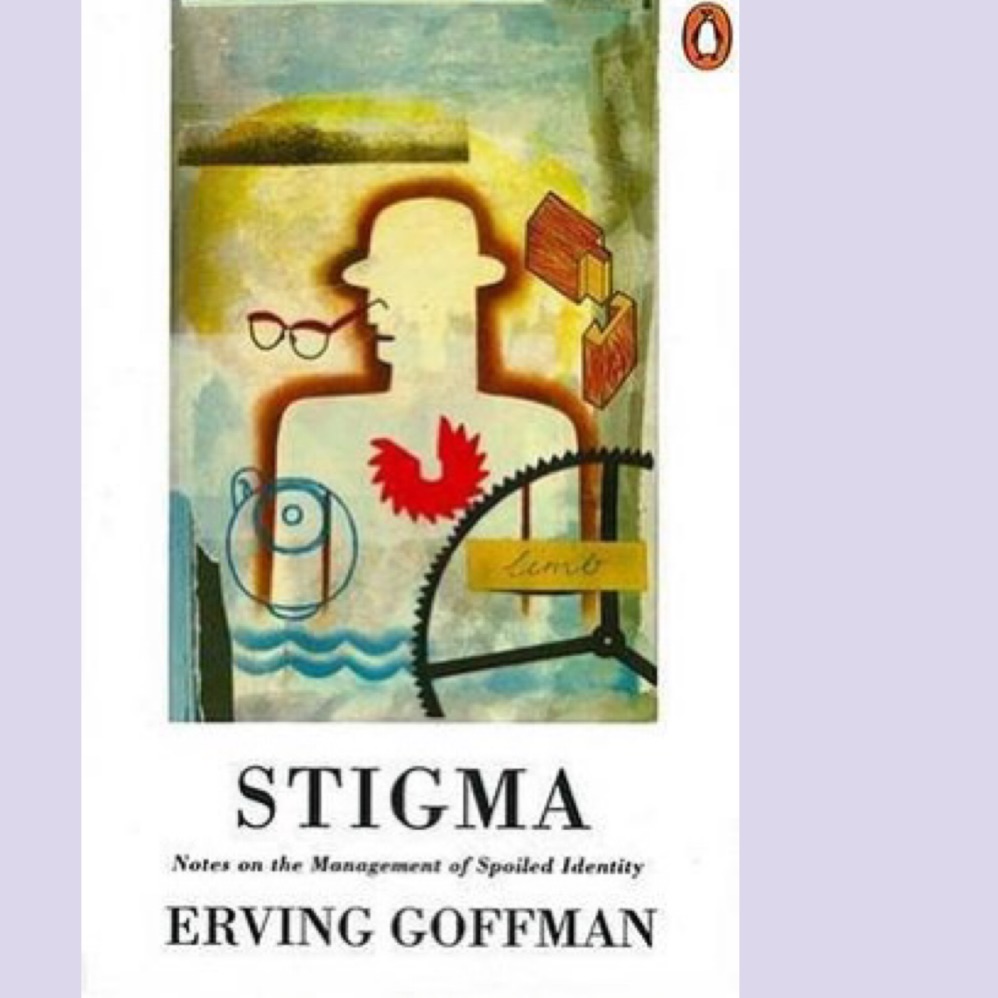
欧文·戈夫曼 1963 年著作《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学者剖析美国社会的偏见:污名化、模糊人、美国理想的背叛者
新近瘫痪的残障人士以残缺的身体和崭新的身份面对世界,这本身会使他重返社会的道路变得微妙而力所不及。在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对残障人士的偏见和对他们社会地位的贬低已经司空见惯。最极端的表现是对他们的回避、恐惧和赤裸裸的敌视。正如欧文·戈夫曼 1963 年在他的著作《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中写道,残疾人与有犯罪前科的人、某些少数民族和种族的人、精神病患者等一样,都处于一个较低的社会地位。一个人要想充分参与社会,最大障碍不是他的身体缺陷,而是社会所附加的一系列虚构、恐惧和误解。
和他的轮椅一样,美国的残障人士必须要面对的那种文化也是他残障环境的一部分。显而易见,残障人士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都违背了美国人所珍视的那种年轻、男子气概、充满活力和身体美的价值观,虽然大多数人很少意识到这些价值观。大多数残障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感觉到别人为此而憎恨残疾人,认为他们是美国理想的破坏者,就像穷人是美国梦的背叛者一样。人们畏惧我们,他们生活在一个伪造的天堂里,他们也很脆弱。我们代表了一种可怕的可能性。使残障人士特别具有威胁性的是投射和认同的心理机制,人们通过这种机制将自己的感觉、计划和动机归因于他人,并将他人的感受、计划和动机纳入自己的感受。
欧文·戈夫曼的“污名化”研究对残疾社会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残障者、罪犯和某些少数群体拥有共同的命运:他们都是局外人,都偏离了社会规范。
对于应该帮助残障者的劝告,我们会在安全距离以外践行。我们向美国出生缺陷基金会和肌肉萎缩症协会等组织捐款,或者向乞丐的杯里扔硬币。这样,身体健全的人既可以安抚自己的良心,又不用靠得太近。他们通过慈善的行为强调与残障者的区隔以及自己的完整无缺。这些相互矛盾的善意和拒绝,使得“如何对待残障者”成为价值观冲突的巨大舞台。
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右)与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左)
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写了一篇题为《模棱两可》(Betwixt and Between)的文章,准确又简洁地描述了残疾人在美国生活中的模糊地位。残疾的人既没有生病,也不完全健康;既没有死亡,也没有完整地活着;既没有脱离社会,也没有完全融入社会。他们是人,但他们的身体存在扭曲或功能失调,使得他们人性的完整性受到质疑。患者在病情好转之前一直处于社交中断状态,而残障者一生也处于类似的暂停状态。他们既不是鱼也不是鸟;他们作为没有定义的、模糊的人,处于一种被社会相对孤立的状态。
据研究报告称,这种不确定的品质、这种对正常存在的背离,导致了研究人员所观察到的人们对残障者的普遍厌恶。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她1966年的书《洁净与危险》中写道,文化象征主义把传统的现实分成整齐的类别,而在许多文化中,偏离这些整齐的分类就会被视为危险。
在残障群体中,彼此之间地位平等,因而会寻求长期陪伴
医院的残疾人康复群体内,人们以前的身份被剥夺,降级到无形中“患者”的状态,任何在这些机构中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患者通常是平等的,他们会忽视对方以前的社会身份差异。
在医院以外的残障者中也有这种平等的地位。在过去十年中,我参加了许多残障人士组织,出席了无数会议,我对其中普遍存在的平等气氛感到惊讶。尽管我经常是在场年龄最大的人,也总是处在最有声望的位置,但这种平等还是延伸到了我身上。没有人称我为“博士”“教授”,甚至“先生”;他们只称呼名字。我对残疾的了解比大多数人都多,这一事实得到了一些尊重,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权威。事实上,我常常懊恼地发现,人们对我的许多观点不屑一顾——这对一个习惯于让听众对他说的每句话都做笔记的人来说,是一个打击。
作为残障者的共同身份覆盖了我们以前的年龄、教育和职业等级,也消除了许多性别角色障碍。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是在1976年接受物理治疗的时候。当时我被介绍给一名腿部瘫痪的年轻女子,我立即问她:“你的治疗进展如何?”她回答说:“我最近哭了很多次。”我接着说:“我根本不能哭,那样会更糟的。”这完全是一个自发的交流,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谈话。我真的对一个刚认识的女士说过这句话吗?后来在康复楼层住院时,我被安排在一个有三名女士的房间里。这种背离传统医院程序的做法是因为医院里人太多了,时间安排也有问题。但我们这些住院人员谁也没有感觉不安。因为我们谁都无法独立从床上起来,如果我或者其中一个女士能够骚扰别人,那才堪称奇迹。
作为受到局限的人,残障者却能以完整的个体身份面对彼此,不受社会差异的影响,而且他们经常坦率地向对方揭示一些惊人的事实。在他们克服了最初的反感(这只会增加他们的孤立)之后,许多人开始寻求彼此的陪伴,这通常是通过加入残障人士组织的方式来进行的,在那里,他们才找到了友谊和逃避边缘世界的避难所。
美国神话推崇个人英雄,摆脱依赖是残疾人努力目标
在我们的美国神话中,独立的个体带来了秩序、正义和财富。英雄是一个脱离了群体生活和文化存在的原生形象,同时他又使群体重新成为一个整体。他代表了一种对拥有独立的力量,以及不受他人影响而能改变他人的能力的梦想。毫无疑问,残障人士是典型的美国式反英雄。

美国电影《兰博》剧照,塑造了越战战场返回的兰博无法融入社会而行侠仗义,成为孤胆英雄,深得美国年轻人的喜爱
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化中,缺乏自主性和对他人的单向依赖会降低人们的社会地位。大多数社会中的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学会分享和互利互惠,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变得自立。摆脱依赖一直是残障人士政治运动的中心目标,许多残障人士通过自身努力发现了自己的可能性。
例如,我们在研究期间遇到了两名年轻女性,她们住在退休住房项目的一套无障碍公寓里。其中一位女士因脊髓损伤导致肢体残疾,她手部严重萎缩,但上半身的力量很好。另一位患有脑瘫的女士,有中度言语障碍,胳膊和手的功能非常受限。尽管这两位女士都使用轮椅,但她们都完成了大学学业。她们曾经住在宿舍里,现在正合租一套公寓。她们两人各自拥有一辆厢式货车,可以自己购物、下厨,满足自己的一应需求。患有脑瘫的女士握不住餐具,就由另外一位女士帮忙喂食。这一切不仅仅是一种可行的生活安排,它更向世界表明,身体上的损害不一定会损害人的尊严和完整性,甚至可能会增强它们。
残疾人唯一的残疾是过早的放弃,这是生命的早亡
我们所有人都在失去自我和失去他人之间,在走向世界和回归自我的内心之间,在生与死之间摇摆不定。很多残障人士已经屈服,并永远生活在他的阴影下。这是生命的一种过早死亡,但这也是大批残障人士失乐园般的领域,他们唯一的残疾是过早地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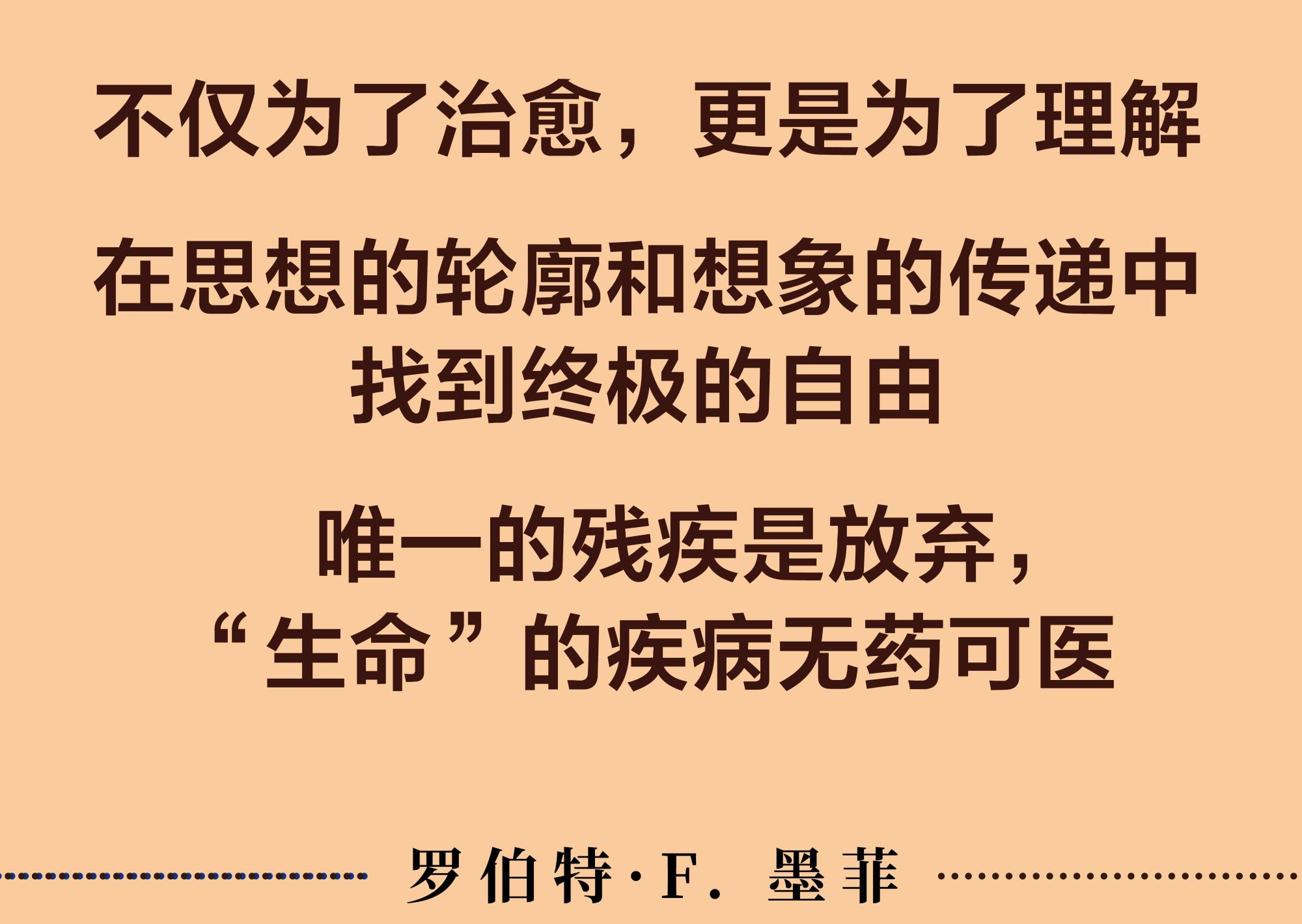
然而,生活的力量——源于复活、饥饿、寻找、自信的厄洛斯(爱欲)——是强大的,有数百万人在身体衰弱的各个阶段,摆脱了依赖的束缚和绝望的吸引力,努力进入那个已经停止对他们人性评判的社会。他们通过相互联系和参与工作,拒绝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和对他们身份的建构。他们正是推进我们这个世纪争取尊严和自由的伟大斗争者之一。
我于1971年首次出版的《社会生活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Social Life)探讨了文化规范的意义与社会活动兴衰之间永恒的矛盾。最终,它不得不以对社会及其对文化形式暴政的蔑视而告终。本书延续了这个主题,通过对本体——存在状态的理解来探索社会中处于瘫痪状态的个人。我发现它在生命的战斗中以最高的形式被包裹起来,以抵抗孤立、依赖、诋毁、混乱,以及所有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把他们从生活中拖出,进入他们的内在自我和最终的否定。这场斗争是人类对生命的愤怒的最高表达,也是我们瘫痪者和所有残障人士的终极目的
从字面上看,残障人士似乎永远是肉体的囚徒,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与生俱来的囚犯。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制造的围墙里,透过文化铸起的藩篱,透过恐惧磨炼出来的铁栏,凝视着外面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脱离之前的环境,重新发现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哪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残障人士——以及我们所有人——将在思想的轮廓和想象的传递中找到终极的自由。
李念编摘自《静默之身》全书各章节
作者:墨菲 邢海燕
编辑:李念
责任编辑:李念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