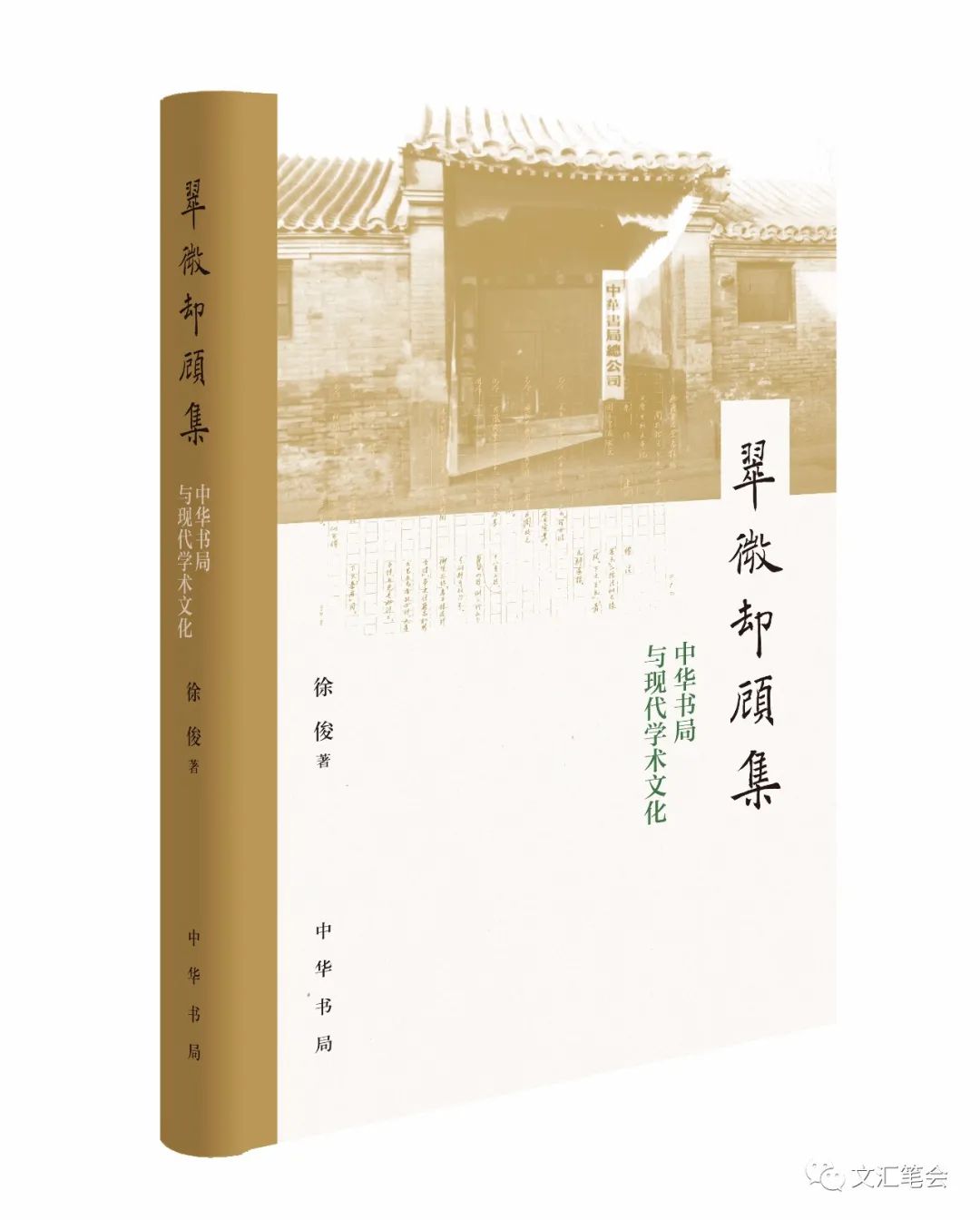
本文系作者为徐俊《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所作序言,该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徐俊同志自1983年入职中华书局以来,经历过许多职务,做过各种工作,阅历丰富。1991年为了纪念建局八十周年,他参与了《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一书的编选,曾仔细查阅了中华书局的旧档。出于他对书法的爱好,精心选录了许多珍贵的名人书信。他是个有心人,我相信这时他对中华书局的局史已有了大概的了解,对这些信的史料价值,比我们许多早入职的同仁了解得更多。例如他把向达先生的九封信全部收入了,二十年以后他又对这九封信作了考证和阐释,为向达先生的学术传记作了重要的补充。
2006年以来,徐俊同志担当了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作的重任,由文学专业出身而已学有专长的老编辑转向了历史学科,在边干边学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对史部古籍整理有了新的认识,成为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新一代负责人。在修订工作开始时就组织人员仔细清理旧档,访问前辈,建立了深厚的文献意识。“文”是书写的记载,“献”的古训是贤人。如孔子所说的:杞、宋二国的文献不足,所以就不能征之为夏礼、殷礼的史源(见《论语·八佾》)。文献才是历史记载的根源。
前贤的记忆还是要靠文字记载才成为“文献”,如蔡美彪先生是从点校《资治通鉴》到启动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程唯一的、全面的历史见证人,真是古人所谓的“献”,要不是徐俊和他进行过多次访谈,就不会写成《平实而通达的引路人》一文,使我们详细了解了《资治通鉴》与“二十四史”整理出版的缘起。此前蔡先生自己的著作没有在中华书局出版,只提出了不少评论和建议,对中华书局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评价很高,他认为新中国学术成绩最突出的是考古发掘、古籍整理、民族调查三个方面,真是高瞻远瞩,独具慧眼。他对中华书局寄予了厚望,真是中华书局的老朋友和引路人。我对此才有了新的认识。
徐俊同志对历史的尊重,对文献的敬畏,对前贤的爱护,驱使他写出了这些充满热情的文章。本书第一篇《王仲闻:一位不该被忘却的学者》,就是产生于重印《全宋词》时查看旧档而产生的感动。他并没有见过王先生,但看到这些审稿笔记,就情不自禁地发愿要把这份笔记公之于世,让《全宋词》的读者都能记起它的责任编辑和参订者。又如他1996年从旧档里看到周振甫先生的《管锥编》选题建议及《管锥编》《谈艺录》的审读报告,深受感动,就用刚学会的技术亲手把近五万字的周先生审读意见全文逐字录入电脑,认真学习,后来就公之于众,显示了他对前辈业绩的珍重,也给编辑界的同仁提供了典范。这些文字里,都深含着他感情的温度。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开始之后,徐俊同志更仔细地查阅旧档,请教前贤,访问老作者的亲属及学生,理清当年每一史的点校过程、体例形成过程和各史特点,尽可能地保持点校本已取得的整理成果和学术优势,在出版之后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足见他对史部古籍整理工作有了深切的理解。最近的一篇《二十四史点校整理的回顾与现状》,也是修订工程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我相信在修订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出齐之后,他还会写出更完整更深入的总结。
“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过程,反映了这二十年间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段历史,也折射了二十年政治气候的变化。必须考虑到,1958年点校工作启动的时候,正是推行“大跃进”的时期,所以宋云彬点校《史记》时,上午还要为炼钢铁而劈柴。历史的进程,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划、计划,赶不上客观条件的变化。因此我们的工作,总会留下一些遗憾,留待后人继续修订。
在主持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工作中,徐俊对史部古籍整理有了不少新的认识。他对已出的点校本,作了全面的调查和评估,并澄清了一些疑问。正如以中华书局编辑部名义写的《修订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缘起》所说的,既保持了点校本已取得的整理成果和学术优势,又如实地说明了修订本的重大突破,最后表明:“成为定本”还需要广大读者的考验和后人的不断努力。
我们出版业的工作人员,永远只能向读者表示这样的态度。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最初是郑振铎先生提出的。毛泽东主席一向号召党政干部要读《资治通鉴》,1953年提出要做标点本,1956年由古籍出版社赶出来了,毛主席很满意,只是批评了精装本太重,拿不动。1958年提出要印“前四史”,以一年为期,经范文澜、吴晗等人请示报告,再扩展到“二十四史”的整理。中央领导只是提出一项任务,本来不会也不必考虑整理出版的具体细节,但进度总是要快。而实际工作的学者,则总是愿意尽自己所能,把工作做得好一些。因而1959年国庆献礼,只有《史记》因为有顾颉刚、贺次君先生的初稿,总算由宋云彬先生赶出来了。点校《三国志》的陈乃乾先生早起还是赶上了晚集,到1959年底才出书。后来前四史到1965年才出齐,主要原因是整理者、出版者都出于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忠于自己的职业操守,想提高学术质量,尽可能提高校勘的要求,追求体例的完善。据说古籍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同志1960年还提出了“成为定本”的要求,压力很大。后来唐长孺先生的北朝四史、王仲荦先生的南朝五史,全面执行陈垣先生提出的“校勘四法”,更增加了整理的难度,拖到1965年也没能出书。这都是学术工作者的一片好心,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后果。直到1976年,毛主席也没有看到“二十四史”点校本出齐,辜负了老人家对古籍整理工作的厚望。
本来吴晗先生等策划的也是先出“普通本”,另出集注本、新注本,这一点恐怕是我们理解不到位,造成了越来越深的深井。吴晗作为明史专家,恐怕也想不到《明史》的标点会遇上那么多难题。
我个人对上级交办的任务,也总想取法乎上,力求保证质量,但往往延误了时间。如1959年接受了编辑《海瑞集》的任务,当时只知道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曾过问此事,吴晗更积极地写了《海瑞的故事》和剧本《海瑞罢官》等,我估计是有上级领导指示的,所以努力做了校勘、标点、辑佚的整理工作,屡次统版改版,拖延到了1962年底才出书,又如1962年3月,周扬曾指示要出老专家过去的论文集和专著,周一良先生的论文集就是一个例子,也因误了时机,到1964年就不敢公开发行了(详见本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出版轶事》一文)。还是1961年,周扬写了一个条子,要出徐文长、汤显祖、郑板桥的集子,交到中华,我又接受了编《徐渭集》的任务。也是一再改版,拖延到1965年才打出纸型。那时文化部已经挨批了,就不敢付印,压到1983年才印出来。因此我的经验教训是上级交付的任务一定要快赶,但又不能草率从事,忙中出错,这使我非常困惑。1973年,我又接受了中央交办的重印《昭明文选》的任务,不敢排印,就提出影印宋刻本的方案,居然被批准了。当时乘机多印了一些,内部卖给曹道衡、袁行霈等专家学者,还办了一件好事。但是排印书还是要认真整理,取法乎上,否则就背离了我们的初衷。
1976年,大概是5月份,出版口下达命令,毛主席要看大字本《李太白全集》,中华、商务当时合署办公,社领导动员好几位同仁加急点校,委派周振甫先生和我负责定稿发稿。这次我们不等全书定稿,分卷发排,流水作业,打出一卷清样就送一卷到中央,大约送出了不到十卷。直到9月8日22点,我和校对科的好几位同事还在新华印刷厂加班校读清样,不料9月9日凌晨毛主席去世了……这次我是急事急办了,可惜还是没赶上。
我个人的一点经验教训,也愿与同仁们共享。顺便写下来作为文献资料,附在徐俊的骥尾之后,借以纪念中华书局的110周年。
本书题名为《翠微却顾集》,化用了李白的诗句,与中华书局上世纪“翠微校史”的佳话相衔接而增加了诗意。“翠微校史”的佳话,最早是1963年王仲荦先生等入住翠微路中华书局宿舍时说起的(王同策先生在《翠微校史的日子里》一文中,记罗继祖先生的话,王仲荦先生曾提议罗先生画一幅《翠微校史图》,可惜没有实现,现存只有一张陈垣先生家里拍的照片。赵守俨先生哲嗣赵珩兄写有《翠微校史:西北楼里的大师们》一文,已传为佳话)。本书里的文章已成为中华书局局史积累的史源文献,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史料的一个部分。因此徐俊把这本书加上“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的副标题,并不是自我夸张。
本书为现代的多位专家学者补写了外传,但不是“儒林传”,而是艺文志的大序。这些文章,都是中华书局局史长编的资料,也是现代学术文化发展史长编的资料。徐俊在清理档案文献中不断提高了他的史才、史学和史识,而他对前辈业绩的热情爱护,则养成了工作中的一种史德。我感到遗憾的是,中华书局有一时期的部分档案,竟流失在外了。徐俊从网络上搜索到了一些残片,稍稍得以补救,也算是拾遗补缺了。
徐俊同志委派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我对这些书和人还略有所知,为“二十四史”只做过极小极少的一点工作,但义不容辞,勉力写了一点随感,聊以应命。通读本书,深为感动,不禁情发乎中,谨以小诗一首为赞:
书共人长久,绵绵史可征。
中华文与献,千载树长青。
2021年11月11日
作者:程毅中
编辑:安 迪、钱雨彤
责任编辑:舒 明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