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30日,中国女科学家颜宁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不久后,网上开始流传一个帖子称,颜宁曾被问及此前落选中科院院士的原因,她回答:“要想入选中科院院士,你可以不是一个优秀的人才……”

此帖一经发布就引发大量关注和讨论。
对此,颜宁本人通过微博回应:到哪投诉这种说瞎话都不眨眼的啊?
颜宁还表示:不理呢,竟有人当真理呢?替ta们抬咖么?以及装模作样表现得跟我很熟的,不知道我最讨厌自来熟么?以后谁提到居老师的时候,非把我和另外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科普博主放在一起说,我要翻脸了啊。

截至记者发稿时,不实网帖已被发帖人删除,发帖人账号也已被微博官方处以“扣除信用积分5分,禁言7天,禁被关注7天”的处罚。

这并非颜宁第一次辟谣了。
据新华社报道,此前,颜宁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就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职位时,有的消息称,颜宁受聘普林斯顿大学是“负气出走”。

随后,颜宁通过微博表示网上关于自己“愤然离开”“负气出走”的一些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颜宁表示,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记者从校方也得到了确认,除了颜宁本人的慎重考虑之外,她也就任教一事与学校各级领导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过去10年,我在清华大学获得了极好的支持,我取得的科研成果甚至超过了自己回清华之初的预期。”颜宁告诉记者,“人们常说居安思危,我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些新的压力,在新的环境中激发新的灵感,在科学上取得新的突破。”
作为一名天才级科学家、大龄单身女青年,颜宁身上有太多标签了。这也让她常常站在风口浪尖。
撕开这一切,其实颜宁只是一个纯粹的人。
不久前,颜宁的好闺蜜,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曾撰文写下了她和颜宁的故事,或许能让我们了解一个真性情的颜宁。
李一诺写于 2014年7月3日:
我们是1996年入学的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按清华的编号,生六班。在清华这个男女比例 7:1 的学校里,我们班33个人,15个女生,是极不正常的正常比例,不过可惜我们班的男生大部分都不解风情……不过这伤心事咱先按下不表。
女生都住六号楼。记得当时入校,一走进那宿舍楼就心凉了半截——黑咕隆咚的大长走廊,吊满了洗了晾着的内裤胸罩,有的还在滴滴答答滴水。楼长大妈上来给每人俩白纸包的粉儿, 一个是蟑螂药,放在床板上,一个是耗子药,放“衣柜”里——所谓的衣柜也就是一个大深抽屉。就这样,我们憧憬已久的清华生活开始了。
我和颜宁真正的“相遇”,是在大一暑假,在六号楼我的宿舍。那时候我自己在成为学霸的道路上(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在避免成为学渣的道路上)遇到重挫(第一年微积分考了个 70 来分吧,高中木有见过的烂分数),所以决定暑假晚回家一段时间,苦逼地自己补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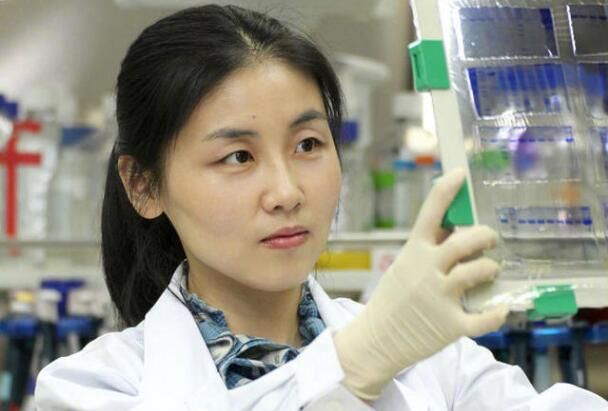
颜宁这个住番外的同班女生竟然也没有回家,而且她的家就在北京!虽然稍微觉得有些蹊跷,不过在清静的校园里有个伴儿一起打饭打水(对那时候要自己提着暖壶打开水)总是好的。所以互相发现的那一天我俩就一起去买饭,然后到452我宿舍里一起吃——顺便带这位番外女生参观一下本部女生的宿舍。吃饭一聊,弄半天颜宁也曾经被微积分所扰,第一学期考试差点垫底,突然感觉同病相怜,一下近了很多(这么说真的要感谢我们的高数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当年的数学神童,促成了我们这段“感情”)。不过拉得更近的,是她的心事,具体是啥我不说。
我和她当时也不熟,也不知道她怎么这么好眼光,知道我是一个可以倾听可以信任的人。我当时就觉得因为有了对方的一个秘密,而突然从陌生人变成了亲近的朋友。现在回想当年,能记住的就是夏天的静静的校园,窗外树上的知了声,和我们俩在宿舍里的这顿午饭。
成了朋友之后,发现我们俩其实是特别不一样的人。我是家里根红苗正,一本正经,有理想有抱负。她是从小学就开始看武侠小说,着迷于各种明星八卦,被正经的我所不齿。我那时候忧国忧民,思考人生意义和价值;她每天沉迷于自己的小世界,为了她的花边电影的选修课到处看电影,每天YY她以后立志要当一名娱记的伟大理想。总之就是我无趣的奔前程,她有趣的无前途就对了。

不过在她的各种不良影响下,我也开始恶补金庸,好像发现了宝藏。而且我被她拉的品味降低,在思考人生价值之余,全力投入到看美女的事业中去——我们俩那时候中午爱去九食堂吃饭,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5字班似乎是水利系的气质超好、酷似奥黛丽·赫本的美女总去九食堂吃饭。我们俩为了看美女也坚持有可能就去吃,直到美女毕业。后来读到女人比男人更好色的理论,深以为然,终于给自己当年的行为找到了理论基础。
在追随美女的几年里,见证了美女和各种不靠谱长相又对不起观众的男生谈恋爱。每次都为她扼腕,感叹清华男生普遍水平之差,导致这个A女陪D男的恶果。不过一直到毕业,我们也不知道这位美女姐姐姓甚名谁,她大概也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俩女生为了看她跑去九食堂吃饭。不过现在想想,当年的简单快乐记忆犹新。
当然我们应该还做很多更有品味的事,但具体是啥都忘了,就是觉得在诺大的校园里干什么都有了个伴儿,是个很温暖的事情。
大二我们俩看4字班5字班的师兄师姐都在上专业课的时候看托看G,觉得如果专业课不学,生物岂不白念了。所以决定早考托考G,以把大三的宝贵时间用来全身心地学习专业课。大二的时候让我老爸帮我们俩报名考托福。老爸辛辛苦苦排队报名,但拼音不过关,填颜宁的名字的时候把 Ning 拼成了 Nieng,而且没法改了。后来我们的宁同学就不得不一路用 Nieng 这个名字申请学校。

不过当时我就很有远见地说,以后你要出名了,这名字肯定好,因为叫Ning Yan的肯定一大堆,但Nieng Yan只有你一个!后来果真,Nieng Yan这个有特色的名字现在成了响当当的国际论文霸啦呵呵。要是哪天Nieng同学得了诺贝尔奖,一定得感谢一下我老爸的说!所以我们俩大二考了托,大三考了 G。觉得大三大四可以对得起自己的专业了,至于有没有,那就另当别论了。
因为我根红苗正,是班里的团支书。她不正经不着调,大二我俩又考完了托考完了G,她在大二开学为了摆脱心事跑去竞选系里的学生会主席,我们那时候小系一个(一个年级就一个班, 后来7字班8字班才有两班),但她竞选成功,突然也成了学生干部。我们俩就这样双双成了“干部”。不过干部这个她不那么当回事的。
后来到大四,我们俩都到诺和诺德在上地的研发中心去做毕业论文。那时候中心的领导是陈克勤(Kevin),温文尔雅的科学家,是早年的 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毕业生。那段经历,是我真正接触科研的开始。颜宁还是每天嘴里跑火车,说话不着调,做实验毁掉整个细胞间。以至于后来Kevin知道我们俩的“下场”,非常惊讶,说以为会是反过来的——我会成为靠谱科学家,而颜宁会成一个每天胡说八道的商界人士,谁知道造化弄人啊呵呵。
大学毕业出国以后,我们一个东岸一个西岸。
美国上学这些年,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俩的生日(俺俩差10天),都忘不了给对方寄一个不值钱但用心的礼物。博士第三年的时候,我们去黄石公园穷游,颜宁从新泽西飞过来,和我们几个UCLA的密友踏上了黄石之旅。一路去了沿途的很多国家公园,照了很多年少轻狂的傻照片。现在回想,那是博士期间最值得怀念的旅行之一。
后来我博士毕业在麦肯锡工作,一次去新泽西招聘,应该是2006年,完事后黑灯瞎火开车去普林斯顿看颜宁。晚上在酒店我房间里一通瞎扯,白天一起去她的实验室,她喜欢的小餐馆,小drug store杂货店买她喜欢的Aveeno的唇膏,还在她的宿舍里,学会了呼拉圈。呵呵记住的都是这些小事情。后来我走,是她送我,在新泽西的火车站,深秋的站台上空无一人,又是一次离别,又有聚少离多的伤感。
再后来我们俩好像计划好了一样,2007年开始往国内跑。我们俩应该是我们班出国的同学里最早回国的。都在北京,不过她初建实验室,我在到处飞做项目。我们俩还是保持了不着调的本性,有一次我正好工作结束在清华附近,一个电话,约到校园里见面。我一身所谓职业女性的装扮,她骑个自行车从实验室过来,穿一运动裤,加上新剪的刘胡兰头,俺俩在紫荆公寓附近的某小餐厅里点了饮料,闲片子扯一通,走人。
要说这么多年俺这友情咋维系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是不着调的性情中人,啥职位、角色,都是我们互相调侃的对象,心里都是傻孩子,我被她带得更有趣些,她被我带得更有追求些,哈哈。我们都是努力工作的人,为了对得起自己和自己相信的事儿,也是为了对得起支持和相信自己的人。但别的很多外在的东西都不那么看中和在乎。由于不在乎,就会有很多简单的快乐,为了丁大点傻事儿能笑的花枝乱颤。这次颜宁发了牛文,电话里喷自己的科研计划,说这是一直在追求的正房,现在搞到手了,下一步就是回去追自己的初恋了。
去年(2013年)生日,我怀着老三,出差回京落地的时候快晚上11点了。给颜宁打了个电话问生日快乐。她说在唱K,问我去不去。我说去,于是直奔五道口,在小包间里和一帮我们大学时代就混在一起的朋友(现在都是叫兽的) 唱些俺们大学就唱的老歌 (新歌也不会唱)。觉得有这么一帮朋友,真心不易。当然高潮在后面,颜宁把实验室的90后小朋友叫过来,看着几个弱不禁风的小男孩和乖乖的小女生,把各种我们木有听过的撕心裂肺的歌唱得七荤八素——瞧这导师当的,多酷!
不过俺毕竟怀着娃,不能太晚走,颜宁送我出来,在K歌走廊的一个角落,有很多小镜子。我们就在那儿,搂着肩膀嘻嘻哈哈地自拍了一张合影。这不是第一张,也不会是最后一张,真实生活虽然各不相同,但坚信俺们会在不靠谱真性情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一路到黑……
最后,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守护好这位天才科学家的赤子之心。至少,也不要去伤害它。
编辑:金婉霞
责任编辑:顾军
来源:综合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奴隶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