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见中国:中西哲学的一次对话》
[美]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 ) [美]德安博(Paul J. D’Ambrosio) 编
朱慧玲 贾沛韬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中国读者早已不会因为一位外国学者的到访而感到新奇,但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到来仍让中国读者兴奋。桑德尔因为网络公开课《公正》而为中国公众所熟知,在2007年到访中国后,更是获得了“通常只有好莱坞明星和NBA球员才能享有的受欢迎度”。
桑德尔说:“我去过很多国家,可能除了美国之外,中国有关自由市场的设想和道德直觉是最深刻的。”桑德尔一直期望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哲学,并从中汲取资源。2016年,桑德尔专程来到中国,与中国哲学领域的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探讨。与会专家从中国哲学当中有关德性、家庭、共同体等观念出发,反观桑德尔的政治哲学思想,指出它与中国哲学思想的可能性关联和冲突。桑德尔针对这些批评或思考,给出了自己的回应。后来,各位学者的与会论文与桑德尔的回应结集成册,就形成了这本《遇见中国》。
《遇见中国》是一部具有启发意义的中西哲学平等对话之作。它体现了自晚清、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两个转向:一是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由全盘接受走向反思与辩证,二是中国对自身传统思想文化,由批判、全盘否定走向重新发现与求证。与桑德尔的相遇,为我们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提供了契机。
迈克尔·桑德尔在《向中国哲学学习》中总结道:“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任何一种相互学习的方案,均应该从接受某种不对称开始。我的朋友、前哈佛大学同事杜维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是一种学习型文明,而西方是一种教导型文明。他在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在称赞西方。我认为他是在说,那些认为自己是在给世界上其他国家传达指令的社会,终会陷入一种狂妄自大。他们的学说会堕落为布道。一种一心从事教导和布道的文明,不仅会招致普遍的憎恨,自己也会丧失面向世界、聆听世界并向世界学习的能力。我很感激这本书的对话者,他们慷慨地贡献了自己的思想,馈赠了批判性的互动。”
>>精彩试读
桑德尔与中国的相遇
文/欧逸文
2012年12月的一个夜晚,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厦门大学的校园里,大批学生聚集在学校报告厅的门外,其人数远远超过了报告厅的容纳量。我站在门里,透过玻璃看着蜂拥而至的年轻学生兴奋激动的脸庞。一批保安在吁请人群保持安静;校长也致电给当晚活动的组织者,提醒他们不要失控。
他们所热诚盼望的对象,在中国获得了“通常只有好莱坞明星和NBA球员才能享有的受欢迎度”(《中国日报》曾这样评价道)。他就是迈克尔·桑德尔,一位温和而善辩的明尼苏达人。他是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他教授的《公正》课程广受学生欢迎,引导学生了解西方思想史当中的核心人物,如亚里士多德、康德、罗尔斯等。桑德尔将这些人的道德决策理论编进现实世界的道德困境当中。刑讯逼供是正当的吗?如果你的孩子需要某种药救命,你会去偷吗?美国一家公共电视节目拍摄了这些课堂现场,并放到了网上。当这些课程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一些志愿者翻译了字幕。两年之内,桑德尔在中国获得了惊人的明星般的知名度。《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称他为“2010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物”。

桑德尔,由Kiku Adatto供图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告诉我:“桑德尔解决道德问题的进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仅非常新颖,而且与某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日常讨论密切相关。”直到我去校园现场感受桑德尔与中国相遇的时候,他那些有字幕的关于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课程,在网络上的观看次数已经至少有2000万次。《时尚先生Esquire》曾经以他为封面,标题是《巨匠与杰作》。
如果生活在21世纪早期的中国(我于2005—2013年在这里生活),就会见证一种哲学和精神上的复兴,这可以与19世纪美国的大觉醒时代相提并论。
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越是得到满足,就越质疑以往的分配方式。为了寻求新的意义,他们不仅从宗教,也从哲学、心理学和文学当中寻求新的方式,从而在一个意识形态上不一致并不断改革的世界当中为自己辨明方向。在一个竞争激烈、由市场驱动的社会中,个体对陌生人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当说真话非常危险的时候,一个人有多大的责任要说真话呢?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定义公平和机会?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在追求繁荣发展那样,唤醒并激发着人们。
桑德尔习惯于和他的妻子及两个儿子安静地生活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市,后来开始学着应对他在国外,尤其是东亚所产生的异乎寻常的反响。在首尔,他曾在一个室外体育场向1.4 万人演讲;在东京,他的演讲入场券被黄牛炒到了500美元一张。在中国,他激发了一种近乎宗教的虔诚,他在这里成为明星般的人物。有一次,在上海机场,护照检查官拦住他,然后喋喋不休地告诉他,自己是他的粉丝。
在厦门大学的报告厅外面,人群聚集得越来越多,最后主办方决定将门打开,以便更好地维持秩序。因此,尽管有消防法规,他们还是让人群涌入过道,密密麻麻的年轻人坐满了每一个角落。
桑德尔走上讲台,在他身后是一块巨大的塑料横幅,写着他新书的名字:《金钱不能买什么》。在这本书中,他询问道,是不是现代生活的很多特征,正在变成他所说的“牟利的工具”。在中国,钟摆已经迅速地远离了计划经济,如今社会上的每一件事物似乎都有一个价签:服兵役、幼儿园上学资格、法官的裁决等等。桑德尔所传递的信息与此密切相关,因而听众全神贯注。他告诉听众:“我并不是在反对市场本身;我是在说,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已经从市场经济变成了市场社会。”
桑德尔提到了从报纸头条上读来的一个故事:某个来自安徽省一个贫困地区的高中生将自己的肾卖了3500美元;当他拿着iPad和iPhone回到家之后,他的母亲发现了这场交易;紧接着他出现了肾衰竭。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和另外8人随后被捕——他们已经以10倍的价格把这颗肾转卖了出去。“中国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桑德尔告诉听众,“不过,每年只有1万个可用的器官。”他接着发问:“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会支持合法地通过自由市场来买卖肾器官呢?”
一个英文名叫彼得的中国年轻人,身穿一件白色运动衫,戴着厚厚的眼镜,举起手表达了一种自由至上主义的立场,认为使肾器官交易合法化会消除黑市。其他人则不同意他的观点。桑德尔突然加大了砝码,假设一个中国父亲先是卖了一颗肾,“几年后,他又要送老二上学,这时一个人来问他,如果他愿意放弃生命的话,是不是愿意把另一颗肾(或心脏)也卖了。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彼得想了想,说:“只要是自由、透明、公开的,富人就可以买到生命,这不是不道德的。”这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我身后的一位中年男子喊道:“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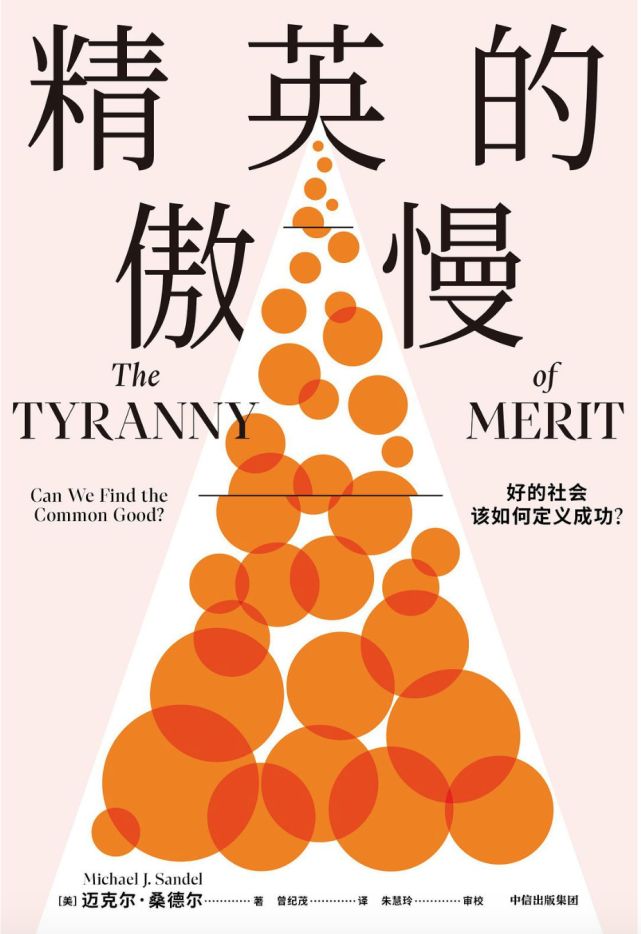

桑德尔已出版作品
桑德尔让现场安静下来,接着问:“市场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我们想要如何一起生活的问题。我们想要一个什么都可以拿来买卖的社会吗?”
第二天,桑德尔告诉我:“我去过很多国家,可能除了美国之外,中国有关自由市场的设想和道德直觉都是最深刻的。”不过,让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与此相对的力量,也就是从人群中传来的对卖第二颗肾感到不安的声音。他说:“如果你通过讨论进一步探究并考察这些直觉,就会发现他们在道德上犹豫要不要将市场逻辑延伸至每一个领域。例如,中国观众一般会接受黄牛票——高价转卖演唱会门票,甚至是公立医院看医生的号。但当我问他们,在春节人人都要回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允许黄牛倒卖火车票,大多数人表示反对。”
在中国,外国思想引发公众关注和学术讨论已经有一段历史了。“一战”后,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封闭的,但它吸引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到访。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汪晖告诉我:“20世纪20年代,很少有著名的西方哲学家来中国访问,除了约翰·杜威和伯特兰·罗素,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和杜威的学生胡适,引荐了他们。”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引荐,杜威和另外几位学者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后来,弗洛伊德和哈贝马斯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2007年,桑德尔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观众已经不再会因为一位西方学者的到访而感到新奇万分,因而互动就需要更加深入,而不仅仅是依靠好奇。汪晖说:“在桑德尔来中国之前,已经有好多西方学者来过了。一些哲学家,像罗尔斯及其正义论,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及其‘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因此,知识分子接受桑德尔的过程,就是一个辩论和协商的过程,这在我看来是好事儿。”进行深入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在介绍桑德尔的时候说,中国有着一颗“急迫的心”。
桑德尔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考虑自己所说的“我们对同胞所负有的道德责任”。他在13岁以前一直生活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郊区霍普金斯,后来随家人搬到了洛杉矶,那里的同学会翘课去冲浪。这强烈冲击着他内心的那种来自中西部的慎重内敛。他告诉我:“南加州对性格养成的影响,能在真实世界不受约束的自我当中看得到。”他早期带着对自由主义政治的兴趣,进入了布兰迪斯大学,随后又获得罗德奖学金的资助,去了牛津大学。一个寒假里,他要跟一位同学合作完成一篇经济学论文。“我这位朋友有着非常奇怪的作息习惯,我大概午夜睡觉,而他会通宵达旦。于是我就有了早晨的时间来读哲学书。”桑德尔这样说道。开学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了康德、罗尔斯、罗伯特·诺齐克和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他最终将经济学放在一旁,转向了哲学。
2010年,中国有一群志愿者聚集到一起成立翻译国外节目。当他们翻完情景喜剧和刑侦剧之后,转向了美国大学那些开始上线的网络课程。桑德尔曾经来过中国一次,给一些哲学专业的学生做过演讲,但当他的课程上线后再次来到中国时,他发现了一些现象。“他们告诉我,如果讲座是晚上7点开始的话,那么孩子们会在下午一点半就开始占座。”他说,“他们挤满了教室,我得小心翼翼地从这些热情的人中穿过。”桑德尔也看到自己的思想在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但都没有像在中国这样强烈。我们讨论过,并试图理解这种现象。哈佛大学的名号当然有号召力,而且公共电视台的专业润色和制作,也的确使这门课程比其他课程观看起来更有趣。然而,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他的上课方式也是一种惊喜:他让学生站起来表达自己的道德观点,让他们独立参与复杂而无限制的问题讨论,这在中国课堂上是罕见的。钱颖一说学生们津津有味地阅读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的中文版,“这部分是因为中国教的西方哲学很少,而且,这本书非常适合中国大学生,它用很多有趣的例子来阐明不同的思想学派” 。
除了上课风格受欢迎之外,桑德尔还更为深刻地解释了中国人对道德哲学的浓厚兴趣。他说:“当社会出问题的时候,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无法严肃地公开讨论各种重大的伦理问题。”年轻人尤其“感到公共讨论的空乏,他们想要更好的”。桑德尔给中国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些有用、富有挑战性但又不具有颠覆性的话语系统,也提供了一个能够在其中讨论不平等、腐败和公平等问题但又听起来无关政治的框架。这是谈论道德同时又不直指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讨论。
有时候,桑德尔会遭到中国评论家的质疑。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反对市场的论证在理论上可行,但“薄”(thin)的公平概念会触动中国人回想起定量供应和空荡荡的货架。另一些人则认为,有钱是保护自己不受权力滥用伤害的唯一途径,因此限制市场只会增加政府手中的权力。“有些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非常气愤地批评他的观点,但大多数听众都很喜欢。”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这样说道,“桑德尔的话题,如正义、平等、道德在人生中的作用等,都与我们这个社会息息相关。”
在厦门演讲之后,我又观看了桑德尔在北京给不同学校的大学生所做的几场演讲。当桑德尔描述说,美国已经分裂成一个富人vs其他人的社会,即“空中包厢化”(skyboxification)的时候,很显然,中国听众在很大程度上感同身受。在昂首阔步地朝着一切皆可买卖的社会前进了30年之后,很多中国人开始反思。
在北京的最后一晚,桑德尔要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做一场讲座。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学生志愿者,他们努力完美地翻译桑德尔的“公正”系列讲座。一个年轻女生滔滔不绝地说:“您的课堂拯救了我的灵魂。”桑德尔正准备问她这样说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人群就拥簇着他去照相和签名了。我犹豫再三,还是走了过去,自我介绍后接着问她。她叫石叶,24岁,即将获得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她告诉我说,当她接触到桑德尔的著作时,就像得到了“一把开启心智的钥匙,并开始怀疑一切”。“一个月之后,我开始感觉到不一样,这已经是一年以前了。现在,我会经常扪心自问,这里的道德困境是什么呢?”
最初她的父母都是农民,后来她的父亲做海产品贸易。“我陪着母亲一起去拜佛,会在桌上摆好供品。以前我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一年后我再次陪着母亲去的时候,我问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的母亲对这个问题感到恼火。“她认为我在问非常愚蠢的问题。我开始质疑一切,我不是在说这是对是错;我只是在质疑。”
石叶已经不再从黄牛那里买火车票了。她说:“当他按自己设定的价格向我出售时,就限制了我的选择。如果不是他定价,我可以决定是买经济舱还是头等舱,但现在他夺走了我的选择权。这是不公平的。”她还开始游说朋友们也这样做。“我还年轻,还没有能力去改变多少,但我能够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
石叶就要毕业了,但她在政治哲学当中所进行的探索,使一切变得更加复杂了。“在我接触这些讲座之前,我非常肯定自己以后会成为一名人力资源专家,在大型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当经理,管理员工。但现在我感到困惑了,我开始质疑自己最初的梦想。我想要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她没敢告诉自己的父母,但暗自希望自己在人力资源领域找不到工作。“我可能会用一个间隔年出国旅行,做一份兼职,出去看看世界。我想知道,我能为这个社会做点儿什么。”
对石叶和其他到了逐渐能够掌控自己的经济和人生的年轻人而言,限制他们能询问什么似乎有些陈旧。接受各种新的观念,包括迈克尔·桑德尔所提出的那些,不仅仅是出于好奇。这代表着要寻求一种新的道德基础,中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寻求应该相信什么。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