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7月18日,北京,大妈手持玩具枪跳广场舞。 东方IC 资料
3月下旬,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将在全国范围推广12套“规范”广场舞,又一次让广场舞和“广场舞大妈”成为关注焦点。2013年年底,关于广场舞的负面新闻陆陆续续曝光,“大嗓门儿、有些发福”的“广场舞大妈”逐渐成为人们侧目的对象。
近日,一篇名为《污名与冲突: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的文章吸引了不少眼球,这是一篇基于田野调查的广场舞研究文章。文章认为,如今广场舞被“污名化”的深层原因有二:一是中老年女性跳舞的行为与社会主流对已婚女性期望的冲突;二是广场舞对公共空间的使用,不合乎现代人对公共空间“安静有序”的期待。“围绕噪音和空间问题的讨论流于表面,‘广场舞’的背后,实应折射出更大维度上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议题。”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王芊霓,是香港中文大学2012级人类学研究型硕士生。她8岁起学习中国民族民间舞,从2013年开始研究广场舞;她在家乡河南做了半年田野调查,前后接触了6支广场舞队,和20多位舞者进行深入采访;回香港读书时,她利用周末往返于香港、深圳,跟着深圳福田区的阿姨一起跳广场舞。
“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也改变了我自己。”4月9日,王芊霓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如此形容自己研究广场舞的历程与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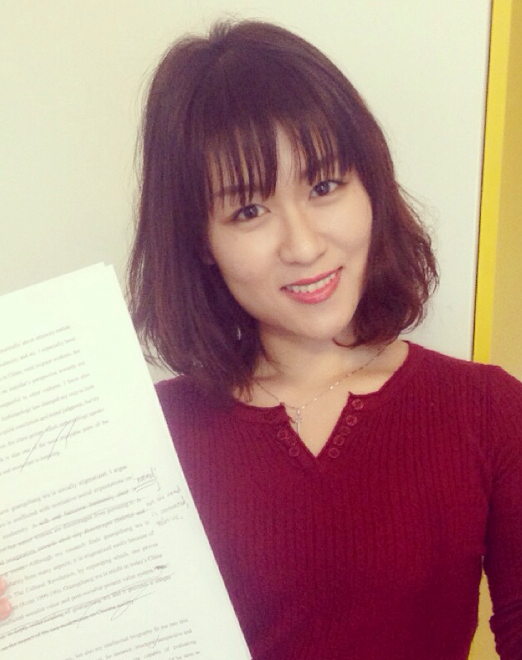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学2012级人类学研究型硕士生王芊霓。
个体化时代的中国,整齐划一的广场舞
澎湃新闻: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广场舞研究?
王芊霓:2013年4月底,我们这届学生在“下田(田野调查)”之前都必须提交一份研究计划。我在第一个学期阅读了许多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书籍,比如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还有他和Mette Hansen等学者关于中国社会个体化等内容的研究,这些书刺激了我对“广场舞”现象的好奇。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个体化大趋势之下,如何解释这种集体活动?
后来我读到《开放时代》杂志上一篇题为“个体化时代的中国式悖论及其出路”的文章。那篇文章提出:“关于中国人的自发联合组织,很多人都在西方的问题情境里思考问题,所以看到的是集体抗争、消费者公民等主题。很少有人关注这样一种现象:在黄昏时分,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广场上,成百上千的人伴随着音乐手舞足蹈,他们排列整齐、动作划一,却可能互不相识。这是在干什么?笔者认为这是私人生活的一种组织化形式。它与网络上的私生活展示行动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型的生活公共化的浪潮。”
正是在这篇文章的直接的启发下,我写了关于广场舞的研究计划,得到了导师们的认可。广场舞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人做过,另外,导师们认为我8年的跳舞经验,恰好可以成为一个受受访者欢迎和支持的研究者,这可能也使我做这个课题比较如鱼得水。
澎湃新闻:通过这项研究,你对广场舞这一议题最大的发现是什么?
王芊霓:对大多数人来说,广场舞大妈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笑料。而这背后,其实折射出社会层面上对女性形象的多元性缺乏包容,也缺乏共识。我认为,参与广场舞的许多女性都可以被称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孤独母亲”。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她们可能刚刚步入中年,就要独自一人在家,她们的丈夫去了收入更高的外地工作,孩子也从高中甚至初中起就到外地就读。现有家庭关系中这些变化造成的孤独,都促成了她们对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关系的诉求。
而这种诉求却和社会期待产生了冲突。一方面,当今的商业化社会塑造着女性对美的认识,刺激着女性追求性感,中老年女性会认为“保持年轻,模仿年轻人在舞蹈中的动作”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而另一方面,传统和保守的回潮,却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趋于抵制这种外显的性感,已婚妇女似乎就该在家“安分守己”。
再一种冲突就是:广场舞与人们对现代公共空间如何被利用的期待产生冲突。在当前社会,以中产阶层为代表的现代都市主流群体普遍认为,一个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应该是安静而有序的。而广场舞代表的一种热闹聒噪的行为方式,显然和他们的期待有所冲突。这个观点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Caroline Chen提出的。
但是,真正的现代性理应建立在对历史的客观辩证认识和对人的基本尊重之上。广场舞议题正考验我们的社会能否在冲突中找到出路,塑造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文化价值体系。
澎湃新闻:落实到研究行动中,你是怎么做这次田野调查的?
王芊霓:我的田野调查选择的是河南省的一个非省会城市,经济水平居中但变化很快,原住民会为了学习和工作去大城市,同时也会有外来移民到这个城市定居,新区的建设也催生了新的邻里关系,这样的城市背后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细节,通过这些细节,可以连通其他宏观的社会议题。
我用了半年时间采访了城市中6支比较活跃的广场舞舞队,并深入到了其中3支。关于个体样本的收集,深入采访2个小时以上的有20多人。这种研究方法能让你真正走入她们的真实场景,通过参与式的观察,形成客观的印象。
在河南进行完田野调查,我回到香港上课,同时继续对田野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周末的时候我去朋友家做客,在深圳福田区一个小区楼下,恰好看到很多阿姨在跳广场舞,所以后来的几个月周末我也经常去她们那里,采访,跟着跳,她们还邀请我参加了她们的一个“看房团”,很有意思。
“依靠真诚和同理心”作研究
澎湃新闻:在和这些广场舞者的交流中,你会注意哪些细节?在采访中你是否碰壁过?
王芊霓:首先,在田野调查时不能隐藏身份,这是学术伦理问题。我们在研究正式启动之前,必须向学术委员会提交一份研究伦理报告并得到批准,在报告中要说明,研究不会对被研究对象造成伦理方面的影响。在技巧上,还要注意避免采访任何熟人,主要考虑到熟人往往忌于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很难敞开心扉。
而具体和陌生受访者打交道时,我好像没有碰过壁。我自己学过8年的舞蹈。因为我的舞蹈动作标准,不少阿姨都愿意和我跳,也会让我教她们一些动作,我也会帮她们录像,陪她们参加比赛,做做后勤工作什么的,这样混熟了以后,她们也向我敞开了心扉。我会和她们分享自己生活中的琐事和烦恼,她们也会非常耐心地倾听,并且分享她们的个人经历与经验教训。真诚和同理心在访谈中是很重要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分享研究者个人经历的这个过程叫“自我暴露法”。
所以我的采访进行地比较顺畅。有一次,我发放一批辅助性的调查问卷,有些阿姨就帮我张罗,让大家帮忙填写。有一次是在晚上,光线也不太好,但那些阿姨还是留到很晚,很认真地帮我填写了,这让我非常感动。另外,我也会用我的研究经费在研究中后期买些小礼物送给她们,是那种可以用来擦汗的可爱的蛋糕毛巾。礼物虽小,但她们都很高兴。
澎湃新闻:一旦深入与受访者的联系,似乎就容易和她们产生感情,你如何保证自己的“客观性”或“距离感”?
王芊霓:首先我不认为有绝对的客观性。基于我的个人阅历、性别、年龄等等,我的研究可能或多或少带有主观色彩。但是这种“主观”如果可以带领研究者和未来的读者更接近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接近一种真实,那就是一种有益的主观。
关于距离感,其实不需要刻意保持,这种“旁观者(视角)”其实并不是强调客观,而是提醒自己要多想想采访者行为背后的原因,而不要把这些行为当作理所当然。另外就是年龄差异,“代沟”嘛,一定是有距离感的。但同时,我觉得人类学家一般都对他们的研究对象抱有“同理心”,这可能是学科的一个特点。
澎湃新闻:你觉得人类学专业对你的研究有何帮助?
王芊霓: 人类学专业和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是我研究的重要基石。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一方面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探求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微观的个体行为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特别强调研究对象本身的“本地人视角”(native perspective),强调呈现社会现象的细节和复杂性。
更多研究集合在一起,才可能接近全面的真实
澎湃新闻:你认为自己的广场舞研究,相比同类研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王芊霓:现有研究似乎多从体育科学的角度出发,关注广场舞的动作是否科学及健身功效。我也看到一些从西方民间组织理论等视角出发的研究。至于媒体报道,太多时候都用“大妈”做标题,让人哭笑不得。我想我的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被访者的“同理心”,能够站在她们的位置和视角去理解她们的行为。
澎湃新闻:我看你的参考文献,20篇中16篇是英文文献,海外资料对你帮助或启发比较大吗?
王芊霓:当代中国研究、性别研究主要还是参考人类学的资料。在我看来,海外研究最大的特点是特别的系统化,每一本新著或是期刊文章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这种承继关系非常好。我也是在现有相关研究,比如秧歌、交谊舞、社会性别、社会空间以及世界其他民间舞蹈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对广场舞的一些思考。我希望我的田野采访资料和我的文章,对同期及后来的研究能有所启发。
澎湃新闻:研究到现在,你的研究心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的研究动力相比当初有变化吗?
王芊霓:研究之初,广场舞还不是一个热点话题。我是2013年6、7月时做的田野调查,而广场舞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大概是在2013年年末。所以,我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并没有所谓“社会污名”这样的预设。但后来,在我整理归纳田野资料和写作期间,它越来越呈现被“污名”化的趋势,我的写作和阅读也不能回避这些问题。一句话,我的研究“被迫”越来越接地气,越来越和社会现实有对话。
未来还不确定,实际上我刚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英文毕业论文正在根据外审和答辩委员会的意见进行最后修订。如果继续研究,我想说不定可以和其他学者有所合作。
如果说我的研究是一部分的真实、一种视角下和一个层面上的真实,那有更多的研究集合在一起,可能会更加接近全面的真实。研究动力当然有变化,现在要更好好写,因为不只是有专业内同行、前辈会看,可能还有一些大众读者对这类研究有兴趣。如果潜在的读者多了,研究动力也会强一些。
来源:澎湃新闻
友情链接 |
|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 上海静安 | 上海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