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有雨的日子,宜读书。这几天寒雨潇潇,落落停停,却读不进去。独自坐在灯下,听着雨声,仿佛回到了住在溪边的日子。
江南的雨,似乎总是飘飘洒洒,慢声细语。有龙卷风的那几天,完全改了性子,几乎要把树木连根拔掉。这样的豪雨狂风,不多见。时光似乎也是如此,有时慢悠悠的,有时锣鼓锵锵,急弦繁管。那种紧迫,就像一个诗人所说:
四十岁到六十岁
这中间有二十年不知去向。
这话有点夸张,“一觉醒来已经抵达/华灯初上,而主客俱老”的感觉,倒是真真切切的,惊心、怅惘兼而有之。
2
住在溪边的日子,就像急弦繁管了一阵子,然后停了下来。忽然之间,很重的东西落到水面上,掀起了巨响,然后慢慢归于平静。这个时候,一尾离开了水的鱼,需要重新回到水里,重新找到自己的河流。独自听着晨鸟的雀跃,独自听着清脆或沉闷的雨声,独自听着窗外蟋蟀的哀鸣,独自观水听风,独自看着夕晖沉没,独自登上天马山……万物静默如谜,涵泳其中,与之交流——忽然之间,发现了那个园子的诸般好处,仿佛无意中发现了自己的河流。
我住的那个园子,离陆机兄弟的华亭谷不远,离醉白池也不远。古华亭本是鹤与鹿的家园,可惜鹿鸣、鹤唳已经听不到了。幸运的是,在那些日子里读到了《一平方英寸的寂静》。这书不仅仅追随约翰·缪尔等人的荒野传统,某种程度上与《达摩流浪者》等书也有一些关联,读了它才真正认识到了寂静已离我们远去。我天真地想成为一名自然声响录音师,置身荒野,倾听最细微的天籁。那本书里有一段话,我很喜欢:“那一晚月光很亮,映照着四周的静谧,感觉就像在聆听一千年前的居民在同一地点听到的声音。他们或许没听过柽柳婆娑的音韵,但肯定听过柳树和三叶杨,还有那些动物的声音。对我来说,那种经验令人震撼,因为我听到的声音跟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听到的声音一样,……”是的,住在溪边的日子里,我听到的也许仍是一千七百年前陆机兄弟听过的声音,也是《诗经》中的诗人听到过的声音,通过声音我遇见了他们,而“声音改变了我的意识”和谛听的方式,——“那一刻的感动就像岩石画或象形文字一样,刻画在我的意识里”。我尝试用文字记录这些声音,记录那些时刻,重新审视自己关于大地的经验,重新估量诗与生活、自然、历史之间的关系。
于是一边倾听,一边观看,一边读,一边写。
3
那年的白露,和友人一起去唱歌,晚上回到那间河边的小屋,疲惫已极,洗了澡便睡下了。除了草丛深处的虫声,万籁俱寂。我的这个小园子,算得上一个微型荒野,除了那个晾衣架和木质桌椅,一切都按照自然的秩序在生长。有时候,把小路上的一些杂草拔掉,才算是略微改变了一点荒野的面貌。
第二天早上十点半,坐在书桌边准备看书,雨便下起来了。沙沙的雨声,真是好听,打在废弃的钢窗上,发出滴滴答答清脆的声响,就像没有节奏的乐音,随意,恬静,悦耳。狗尾草的穗子现在更饱满了,低低地弯下来,在雨中静默着。它们已准备好了种子,随时将它们传送到远方。它们是野蛮、骄傲而优雅的,在枯黄前尽情地展现自己的翠绿,没有虫声里渐渐增加的焦灼。杂草还零星地开着些小黄花,花上面依然翻飞着菜粉蝶。
十二点三刻,我正坐在窗前写一段笔记,不远处的树上传来了寒蝉的嘶鸣,我的心里忽地泛起了一阵喜悦。古人认为,一到白露时节,蝉便不再鸣叫了,其实不然。一声落下,一声又起,只是确实没有上周的叫声那样强劲,收束的时候也有些狼狈。寒蝉唱罢,一只黄中带红的蝴蝶停在那棵细细的桑树上,就像一朵静谧之花。我正看着它,寒蝉的声音又响起来了。那只蝴蝶似乎受了惊,飞起来,环转了一下,落在另一片桑叶上。原来那是一对蝴蝶,它们停下来,又飞起来,在杂草中间欢快地飞着。
下午三点十五分,一只蝉又叫了起来,比上一次还要短暂,但紧接着又开始了嘶鸣。那声音里夹杂着些颓唐、倦怠的东西,也许是刚下过雨的缘故吧。即便白天,蟋蟀依然会倔强地鸣叫。它们似乎不太关心什么时候鸣叫更高效,全天候地发出自己的信息。
窗外,狗尾草长了一园子。门口也是。《古诗十九首》其一云:“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读之令人泪下。
这便是平常的一天。
4
在阿尔克马尔的一个医院里,日本艺术家川俣正开展过一个艺术项目,造了一座木桥,名为“工作进程”。这座桥由艺术家与患者共同建造,过一段时间就要延伸一次,不断地处于更新中,仿佛可以感受到地平线彼端海的气息。这是一条多方向的、让医院的病人象征性地重回社会的隐喻之路,听觉、视觉、嗅觉、触觉本身被激发出来,成为景观的一部分。步道的高低起伏,改变着人们看的视点,木头的声音让人们感知到新的声响。
偶然看到这件作品的图片,让我对读与写有了新的思考。每一本书,都是一条这样的通道,让读者看见那些未曾看见的风景,关于自然、社会、心灵、自我、历史等等。每一条通道,都留存着作者观看的方式,显现着眼睛的历史性。因此,阅读是一次观看,一次体验,一次感觉,一次参与,一次搭建桥梁的行动,一次“自私”的发现。每一条通道,都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建造的,作者敞开了可能性,读者参与进来,丰富、充实了这种可能性。写与读,便是与世界建立关联,接收并传递来自“前方”的口信,建立一条可能的逃逸线,——这是读与写的归依之处。回头看自己的写作,自然很不满意,甚至是失望的。以后不会再写那些考据性的东西了,也许它们增添了一点儿对于古人的了解,然而对于踏实的生活实是可有可无的,或者说,那只是一种不良的写作趣味的结果。知识很重要,能带来愉悦或解答,沉醉其中则是一种自欺。对每个渴望自我觉知的人来说,启迪高于知识,只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通道,浸润在生活的河水里,才能略略接近那看不见的风景。
读与写,是存在的方式,是寻找逃逸线的方法。
5
收在这本书里的几十篇小文,要算是从逝水中抢救出的证据。过去的十几年,读书没有什么计划,写东西凭兴致,乱七八糟的东西写了不少。回头看看这些文字,未尝不浸透了一些生命的欣悲,有价值的却不多,更不能确信对他人有益。作为“证据”,成色不足。不过,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悲欣,不期待大悲大喜,也没有强烈喷发与风生水起的欲望。倘若说有点自己的追求,便是平淡些,再平淡些,却又每每因清浅而缺少后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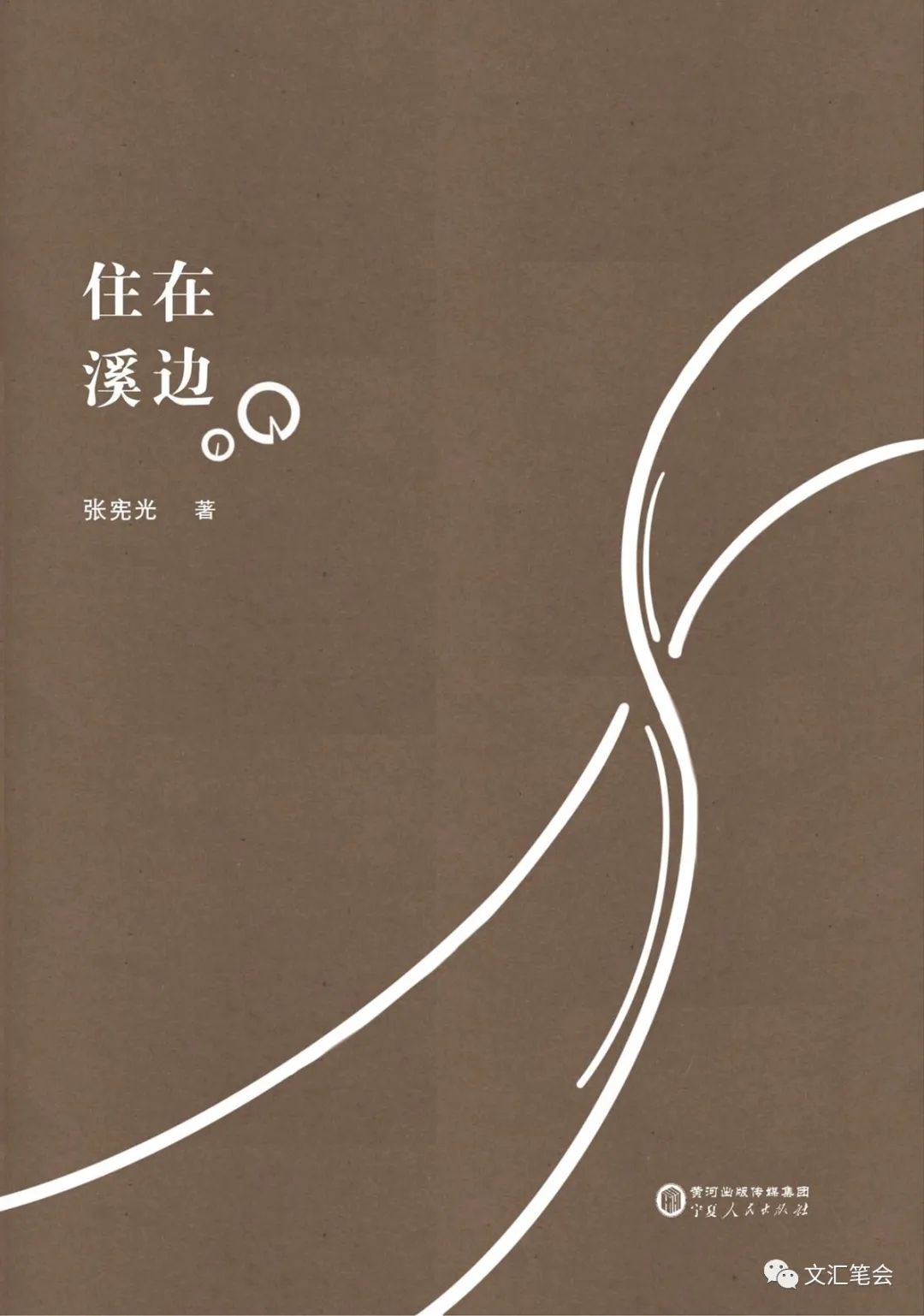
保罗·策兰的诗里说:
你改变钥匙,你改变词语,
和雪花一起漂流。
什么雪球会聚拢词语
取决于回绝你的风。
那回绝你的风,是生活的恩赐,让你和雪花——词语一起漂流,一起进入一种边缘的状态。在边缘中寻找词语,是一条孤绝的路,也许要不得不沿着它走下去。我影影绰绰地看到了那无法言说的“雪”。
(本文为作者《住在溪边》一书自序,该书即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张宪光
编辑:吴东昆
责任编辑:舒 明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